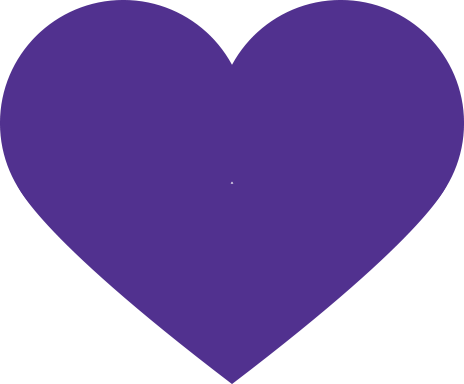
| 第六章 |
你只是替代品
我不仅得陪着老太太演戏,
还要陪着林越深演戏,
我容易吗?

半途苏珊珊接了个电话,然后就急匆匆地把我甩了,我连拜托她帮我留意有没有熟识的幼儿园工作人员什么的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我跟夏云估计得彻底变成陌生人。爸妈还在监狱里蹲着,奶奶一年前也走了,我现在就只有夏雨一个亲人了,就算真的跟老太太吵上一架,我也坚决不能把夏雨送去国外。
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已经出了酒店。街上突然下起大雨,急促而凶猛,雨滴砸在皮肤上,凉透了。我侧过头,看见商店橱窗里自己晕了水汽的脸,恹恹的,有些苍白,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
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在找地方躲雨。我忽然被人重重地撞了一下,对方人影一闪,头也不回地跑了。我抚着被撞的胳膊,回头望了那个人一眼。我其实是想提醒他,他的东西掉了。
我往地上一瞧,发现那是一本杂志,大约是掉在地上才翻开了。我愣愣地看了几眼,居然发现上面的人是林越深和我,还有夏雨。那天在动物园的照片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杂志上,配着密密麻麻的文字,三个人手牵着手,居然带了那么点温馨的味道。
我想看清楚一点,可杂志已经被迅速涌来的人群踩了好几脚,然后淹没在雨水里。
我脑袋里忽然闪过异样的感觉。我记得林越深一向不喜欢家里的人上报纸、杂志什么的,就连当初结婚也鲜少有媒体曝光,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被登在杂志上?
“夏果。”我还没好好想清楚,一只手突然袭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腕,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然后用力一扯,逼得我不得不面向他。
这场景就仿佛电影里所有没有声响的慢镜头那样,冰凉的雨水、拥挤的人群、氤氲的雾气,以及雾气里那张记忆中的脸——
下巴削尖,嘴角好像永远都是倔强地往上翘着的,鼻梁高挺,睫毛又浓又密,被雨水打湿后,伏在眼睑上。
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夏果。”傅靖痕又叫了一声,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我。我看见他胸膛一起一伏,伴着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
然后,我就傻了。
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特别冷,我鼻子一酸,视线就更加模糊了。我跟傅靖痕像两个真正的傻瓜一样站在汹涌的人群里一动不动,那样贪念着彼此。
我回去后就感冒了,不停地打着喷嚏。老太太看了一眼跟落汤鸡一样的我,又训了我一番。我身体不停地发抖,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用人端着姜汤过来,我捧着碗的手都是颤抖的——太冷了,冷到骨头里了。
“夫人,您先沐浴,把衣服换了。”我愣愣地看着巴塞洛缪恭敬而又温和的脸,他的嘴唇在动,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傅靖痕,傅靖痕,是傅靖痕对吗?
刚刚是傅靖痕。可是我跑了,我一甩开他的手就死命地跑,跟只兔子似的,又急又快,跳上出租车报完地址就回来了。
他在追。他真傻!雨那么大,他像疯子一样追着车跑什么?他以为他在拍电视剧啊?
他真傻!傻透了!跟以前一样蠢!太蠢了!
“夫人,夫人。”巴塞洛缪还在说话,我呆呆地看他一眼,然后进了浴室。
花洒下的水滚烫,身上的皮肤仿佛都要烧起来了,眼泪混在里边,落在嘴唇上有点咸。我觉得我可真是没出息,上次见到姚倩也是这样,跟欠人钱似的拼命躲。不是说清楚了吗?不是已经分手了吗?有什么好躲的?真是没出息!
没出息透了!
我调整好情绪,裹着浴巾出去。林越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就那样坐在沙发上,听到响动后,抬眸看了我一眼。
那是极深极深的一眼,仿佛寒潭。
“你的电话。”修长的手臂白皙得可以隐约看见皮肤下的青筋,纤长的十指微微弯曲握着正在振动的手机递过来。
我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林越深的表情,他微微抿着嘴唇,下巴绷得有些紧,高挺的鼻梁下一张脸轮廓清晰得仿佛希腊雕塑一般,长长的睫毛伏在眼睑上,遮住了眼睛,因此我也弄不清他此刻的情绪。
我接过林越深递来的手机,触到他指尖,他的指尖冷得像冰。
一串熟悉的号码映入眼帘,我的心急促地跳了几下——是傅靖痕!
我当即把电话挂了,手都有点发抖。
“怎么不接?”林越深声音低沉,眼睛微微一眨,然后看向我,好像早已经把我看透。
我捏着手机,就这么一两秒的时间,觉得手心都浸出汗来了。
“不认识的,大概打错了吧。”我又想逃,心想:他怎么突然回来了?
“过来。”他解开领带,把亚麻衬衣的纽扣松开一两颗,露出一截诱人的肌肤,然后朝我伸出手。几步之遥的距离,我几乎只要把手伸出去就能触到他的指尖。
可是我就是觉得危险,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偏偏这个时候,手机再一次响起来,机身突然的振动吓得我差点直接把它扔了。
“接!”林越深的眼神陡然锐利起来,连薄唇吐出的字都是锋利的。
我打了个寒战,立马哆哆嗦嗦地按下接听键。
“夏果,我现在发现你们可真是姐妹啊,都跟我装是吧?我苏珊珊真是瞎了眼才认识你!”苏珊珊的声音一传过来,我就觉得天下太平了。我从来没觉得苏珊珊的声音这样好听过,以至于我压根就忽略了她说的是什么。
“你说什么呢?”我转过身,背对着林越深轻轻呼出一口气。
“还跟我装呢?你刚才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笑啊?我跟个傻子一样被你们姐妹玩!”
苏珊珊这番话太莫名其妙了,我也怒了,没头没尾的她冲我发什么大小姐脾气呢,于是我说:“苏珊珊,你忘吃药了吧,抽什么风呢?!”
苏珊珊就冲我吼,我在电话这头都能感受到她的怒气:“你才抽风呢!你装什么呀?你姐和顾肖都要私奔了,你还跟我装!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在万泰酒店,当场抓的现行!你姐跑哪儿去了?是不是找你去了?”
我有点消化不了苏珊珊突然给我的一连串信息,怎么又是顾肖又是私奔的?
我打了个喷嚏,觉得脑袋被苏珊珊绕得有点晕:“什么私奔啊?怎么又扯到你家顾肖了?我没听明白。”
“你不明白谁明白?你就跟我装吧,我算是看清你了!你给我告诉夏云,有种她就别出来,否则我连她和那个小孽种一起撕了!”
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我握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突然一个激灵,转身去看身后的林越深。
“我姐跟顾肖……你知道?”我就是觉得林越深是知道的,夏云老公那事也肯定是他干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巧?
林越深挑了挑眉,不置可否,他又拍了拍身边的空位,示意我坐过去。
我挪过去坐下,不动声色地跟他隔了一点距离。他伸过手来闲闲地卷着我的头发,声音淡淡的,但我就是看见他漆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戾,转瞬即逝。
我身体僵了一下,突然有点同情夏云的老公。依林越深的手段,应该远不止于此吧。
“阿嚏——”我又打了一个喷嚏。我觉得我肯定感冒了。
林越深探了探我的额头,睫毛微微垂下来:“听说你是淋着雨回来的,怎么回事?”
“雨下得急,没躲开。”我脑袋有点晕,也就不去计较他的手了。其实,我的额头那样烫,被他凉凉的手指摸着还挺舒服的。
“去吃药。”
我想起自己刚才还在电话里让苏珊珊吃药呢,因此,现在听到这句话,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
“我没病。”估计我接得太快了,林越深听出来了,侧过脸,轻笑了一声。
“我去睡觉。”我站起来,跟兔子似的直接朝被窝里钻,把头也裹了进去。
我想着,这病生得挺值的,起码今晚不用应付林越深了。
不知道傅靖痕有没有着凉?应该没有吧,他的身体可一向比我好多了。我记得毕业那年我们去爬山,也是突然下起雨,到了山顶我就感冒了,冷得身体直哆嗦。在山里手机压根就没有信号,傅靖痕就把我抱进帐篷里,把所有能取暖的都盖在我身上。可我还是冷,他就只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了,钻进来,用滚烫的身体紧紧抱着我。
那一晚,我是听着傅靖痕的心跳声睡过去的。年轻的身体,沾染着山间的青草香,味道熟悉而陌生,却温暖得不可思议。
我裹在被子里,模模糊糊地回忆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一沉,就睡过去了。迷糊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伸进嘴里,固执而强硬,然后有苦涩的味道在唇舌间化开……
没过几天我就接到夏云的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平静而优雅,带着惯有的矜持与骄傲。
我略略想了想,就答应了这场会面。
地点仍是一家酒店,却不是万泰。夏云穿了一件欧式风衣,鼻梁上架了一副大墨镜,一头栗色鬈发披在肩上,只露出半张保养得宜的脸。她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翻着杂志,看起来倒像某个躲着狗仔的明星。
我一屁股坐在她对面,向服务员要了一杯橙汁。
夏云笑了笑,她把脸上的墨镜摘下来,然后我看见她的眼睛,那样漂亮的一双琥珀色眸子,水晶葡萄般嵌在眼眶里,此刻却含着浓浓的鄙夷与怨毒。
她挑了挑眉,说:“我以为你不会来的。要知道,你最擅长的不就是逃避吗?”
我冲她扯了扯嘴角,她漂亮的瞳孔里就映出我尴尬而又苦涩的微笑。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夏云面前真的跟一只丑小鸭似的,就好比,在这种场面,夏云总是能驾轻就熟地保持她天鹅般的优雅,而我,真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她。
“人会变。我以前觉得你再过分至少也有原则和底线,可你看你现在不是就没有下限吗?”我垂下眼帘,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些,而不是当场给她两耳光再走人。
夏云笑了,她笑起来确实很美,就像苏珊珊以前偷偷养过的罂粟花一样,带着那么一股妖娆的魅力。
“没有下限也是被你妈逼的!你妈特别擅长演戏,而且场场精彩,跟个戏子似的。而你,显然没遗传到你妈妈的基因,又蠢又傻,跟你爸夏正明简直一模一样!”
我手握着盛满果汁的杯子,握得很紧,忍着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它朝对面那张漂亮的脸蛋儿泼过去。
苏珊珊说得对,我真被老太太“教育”好了,要搁以前,我早就两耳刮子朝她甩过去了。
“怎么,又想跟我动手?你先看看这些再说吧。”她扬了一下嘴角,露出冷冷的笑容来。
我瞟了一眼,是那天在大街上瞅见的那本杂志。我当时还好奇这种照片怎么会被登出来,这不像是林越深的作风。
“好温馨哪!”夏云的指尖缓缓摩挲着那些照片,“要不是你那天跟我说你在林家的状态,我还真以为你过得特别好、特别幸福呢!”
我突然觉得对面的夏云有点不正常,难道是她最近压力太大,受的刺激太多了?
“你想说什么?我过得好不好、幸不幸福关你什么事?你脑子坏掉了吧!”
“你觉得你配幸福吗?你配吗?你这辈子都该替你妈赎罪!我妈当年从你妈那儿受的罪,总有一天会统统报应在你身上的!”夏云恶狠狠地瞪着我,用她漂亮的、盛满怨毒的瞳孔,“你看,报应不是来了吗?你以为林越深娶你是因为喜欢你?得了吧!我们家什么门第?林家什么门第?哈哈,夏正明当初还特别兴奋能攀上林家这根高枝,却根本不晓得是自己后院起的火。你知道当初夏正明贪污的证据是谁送上去的吗?就是你妈,你那个跟戏子一样成天做戏的妈!”
我整个身体都震了一下。虽然我不相信夏云说的,可就是有一股寒意从脚尖蹿上来,冷冷的,顺着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逆流而上。
“你逻辑学没学好吧?我妈为什么要那么做,把自己也弄进去?”我端起果汁喝了一口,努力想要甩掉那种荒唐的感觉。
“疯了呗!换成是我,我也得疯。好不容易把前妻气死了,自己转了正,谁知道男人在外面又养了一个,还生了个儿子。外面那个成天打电话劝你妈离婚呢!她能不疯吗?”夏云玩着自己的水晶指甲,声音凉凉的,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我脑袋里全是嗡嗡的声音,有点消化不了这些信息。
我一直以为我妈不知道夏雨的存在,要不是我爸进了监狱,怕夏雨没人照顾,我也压根不知道还有夏雨这个人。
可是,我妈知道夏雨,一直知道,连我爸都不知道她知道。
“你妈要拉着夏正明一起死,还要设计你嫁给林越深。你当初是不是觉得自己放弃傅靖痕嫁给林越深救你妈特别伟大啊?”
“可是,林越深为什么要娶你?他凭什么要娶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人?要不是你命好,长了一张跟他前女友相像的脸,你以为他会正眼看你?看看吧,我也是最近才看到的。这个女人,将是你后半辈子最大的噩梦!”说完,夏云砸了一本杂志过来,估计就是刚才她自己翻的那本。我没动,她话里的信息太多了,我真没办法一下子消化。我就是觉得挺冷的,身上的骨头一根一根都在打着哆嗦。
“她离婚了,最近刚回国。林越深最近是不是对你特别好啊?我估计他是想气气她。夏果,我可真替你悲哀!以前你是你妈手上的棋子,现在你是你老公手上的棋子。也是,蠢货除了做棋子被人利用外,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了。”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眼神轻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对了,”走之前,夏云顿了一下,说,“我还要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还真难跟那头猪离婚。可惜了,我本来想的是你肯定得被他糟蹋的,没想到让你逃出来了。现在好了,我离婚了,再也不用对着一头猪过日子了。而夏果你,我就等着看你遭报应!”说完夏云就走了。我呆愣在位子上没动,全身的力气好像都被人抽光了似的,我连揍夏云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波一波的狗血洒过来,我觉得我都快被淹死了。
良久后,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外面走。途中我撞翻了一名服务员的托盘,我呆呆地蹲下去捡,我说:“对不起啊。”说完后我就被吓到了——我的声音特别哑,跟哭了似的,可是我压根就没哭。我怎么可能哭呢?夏云她就是个疯子。
“小姐,您别动,会被扎伤的。”她还没说完,我就感觉整个手掌都疼了一下,血珠密密麻麻地往外冒,我看着看着,就愣了。
疼,特别特别疼。
手机响起来,在包里不停地振动,我呆呆地按下接听键。
仿佛没料到我会接得这么快,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试探地叫了一声:“夏果?”
那是熟悉的、仿佛做梦一样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手上的血珠,说:“傅靖痕,我疼。”声音嘶哑。
傅靖痕是半个小时后到的。那半个小时里,我坐在酒店的沙发上,落地窗外的阳光将整个车水马龙的街道照耀得灿烂而明亮,我看见各种各样的脸:微笑的、悲伤的、幸福的、麻木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张脸。
傅靖痕先给我手上的伤口消毒,然后拿工具小心翼翼地挑我手心里的玻璃碎片:“你瞅瞅你,老是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的,跟个小屁孩似的。夏果,你怎么一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要说你自虐吧,我还真没见过拿自己手指扎玻璃的,你别出心裁啊……”他巴拉巴拉说一大堆,跟个老妈子一样。
我忍着痛,别过脸,说:“有那么严重吗?就扎了一下,你别搞得跟做手术一样,我看着心里发怵。”
“你总得让我把玻璃片儿挑出来啊,要不等伤口感染就有你受的。唉……我说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有那么疼吗?装得太像了!”
“呸!我拿玻璃扎你一下试试,然后再帮你挨个儿挑!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好好挑你的!”说完我就顺便踹了他一脚,他反应跟以前一样慢,被我踹个正着。
他夸张地怪叫了一声,横了我一眼,我朝他扬扬脖子,他就不敢造次了,垂下眼帘乖乖给我包扎。阳光从落地窗斜斜地洒落进来,镀在他那张年轻而生动的面颊上——熟悉的眉眼、熟悉的语调、熟悉的动作、熟悉的气息、熟悉的傅靖痕,仿佛我们之间并没有分开三年时光,仿佛昨天他才把我送到家门口,两个人恋恋不舍地道别,约好今天再见,仿佛我们还是可以彼此拥抱、亲吻、依赖的情侣。
餐桌上的白玫瑰散发着诱人的芬芳,酒店餐厅里有人点了浪漫的小提琴曲,曲调优雅而缓慢,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既温暖又明亮。
我把头仰起来,极轻极轻地呼吸着。我鼻子很酸,努力把想要从眼眶里涌出来的液体逼回去。
再像又能怎么样呢?再熟悉又能怎么样呢?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我跟他毕竟隔了漫长的三年,而且,我还是个已婚妇女!
“行了,好看不?”傅靖痕仔仔细细地将我的手包好,得意地跟我卖弄。我哼了一声,不敢说话,我害怕一说话声音是哑的,那样准得让他看出来我在哭。
傅靖痕摸了摸鼻子,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良久后他的手指才抚上我眼睛,节骨分明的手指,指尖带着不可思议的热度。他笑着说:“行了,夏果,想哭就哭,忍着多难受啊,别憋坏了!跟我你还怕矫情啊?”一说完,他眼睛就红了,跟呆子一样看着我,好像怎么都看不够似的,指尖缓缓在我面颊上摩挲。
我憋着一口气,难过得要死,却还是梗着脖子说:“谁矫情了?你才矫情呢!”声音已然带着哭腔。
“行,我矫情,我矫情行了吧?乖,你就好好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想多大声就多大声,他们谁敢笑你、说你矫情,我就去收拾他!”
我被傅靖痕这话逗乐了,又想哭又想笑,可是胸口堆积了那么多的难受、那么多的委屈,我觉得整个人都快爆炸了。
“乖,夏果,你好好哭,把你的难过哭出来,把你的委屈哭出来,我听着,都听着!谁让我把你一个人扔这儿,谁让我当初没把你带走呢?我活该!看着你难受,我活该这么心疼!”
他一说完,我就真的哭了,哇的一声,跟个小孩似的。傅靖痕把我抱在怀里,手轻轻拍着我的背。我埋在他胸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很快他的衬衫就被我的眼泪打湿了,黏黏腻腻的。可是,我一点都不想放开他,这味道太熟悉了,这是傅靖痕的味道。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闻到了,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拥抱了。
我哭了整整半个小时,哭到最后,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哭什么。我把头从傅靖痕怀里抬起来,抽抽噎噎地看了一会儿他那件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衬衫:“怎么办啊?估计没法穿了!”
傅靖痕摊了摊手:“怎么办?凉拌呗!难道穿一件湿衬衫我就不帅了?”
我憋不住笑了,立马说:“帅!”
“哭完了,舒服点没?”
“嗯。”
“是不是觉得饿了?”
“嗯。”
“那走呗,待这儿干吗呢?走,咱们吃东西去。”说完,傅靖痕就拉着我起来,拔腿就往外边走。
我说:“这儿不是有吃的吗?去哪儿啊?”
“你爱吃这儿的东西?”
“不爱。”
“夏果,你最近是不是又没做检查?我怎么觉得你脑子越来越不灵光了呢?”
“你脑子才不灵光了呢!傅靖痕,我说你怎么那么爱折腾呢?我哭累了,不想走了。”
“那我背你。”
“谁让你背了?我才没那么矫情!”
“我矫情,我矫情行了吧?我矫情得想背你行了吧?”
“滚!我自己有腿!”
“……”
那天下午,傅靖痕开车穿越了大半个城市带我在一家店吃了酸菜鱼,老板居然就是高中时在我们学校附近开店的那个胖叔叔,我们当时都直接称他“胖胖”。高三的时候,胖胖就搬走了,我那会儿还常常跟傅靖痕抱怨以后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酸菜鱼了。
胖胖还认得我们,送了两瓶啤酒,另外多加了很多野山椒。他激动地说:“果子是吧?我还记得你!啧啧,无辣不欢的主儿,跟你叔叔我一个德行!吃好喝好啊!没想到你们真的还在一起啊!”
我跟傅靖痕对视了一眼,彼此觉得尴尬,但都没解释。
正宗的野山椒辣得我眼泪唰唰地往下掉,傅靖痕跟亲眼看人自虐似的看着我,不停地给我递水。他感叹道:“夏果,你还是这么生猛啊!”
我踹了他一脚,喝完水后问他是怎么把胖胖找到的。
“你求我啊,求我啊!你求我我就告诉你!”他这样子特别贱,让我忍不住又想揍他了。
傅靖痕最后还是没告诉我他是怎么找到胖胖的,他微微垂着头,一直专心致志地帮我挑鱼刺,自己倒不怎么吃。等他把鱼眼小心翼翼地挑给我的时候,我的手顿了一下。
以前每次吃鱼,傅靖痕都把鱼眼挑给我,我还骂他烦,早告诉他我不吃鱼眼了,恶心巴拉的,偏偏他像跟我作对似的,每次都往我碗里夹。
后来,那是跟傅靖痕分开一年多以后,我无意间听见苏珊珊说才知道,原来鱼眼是挑给自己心爱飞人的。
我埋着头,默默地把鱼眼吃下去了。
我是天黑之前回的家。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跟傅靖痕道别的,只是迷迷糊糊地听他唠叨:“说了要做朋友的,所以,夏果,以后你再不接我电话,再看见我就躲,可就不厚道了。哎,我说你听没听到啊?给我点反应啊!唉,你脑子真不灵光了啊!”他啰唆了一大堆,我被野山椒辣得压根没工夫理他,只得频频点头。
暮色降临,老太太喜欢养花,前院倒是一片花团锦簇的景象。
我在玄关处换拖鞋,替我拿着包和外套的用人说:“家里来客人了,老太太正陪着呢。”
我的动作顿了一下,客人?一般有客人来的话,无论我在哪儿,老太太都得把我召回来作秀,今儿怎么不用我陪了?
我本来想着不去了,但转念一想,依老太太的性子,她要是知道我回来后不去打个招呼的话,估计又得谈谈我的家教问题,所以,我换了一身衣服,再看了一下夏雨后,就径直去了会客厅。
老太太坐在宽大的意大利沙发上,从头到脚连指甲缝儿都透着一股子贵妇的优雅,保养得宜的手指缓缓摩挲着咖啡杯沿,嘴角含笑,那笑容怎么看怎么敷衍,眼神也是漫不经心的。我一看就觉得老太太不太待见这位客人,难怪她没把我召回来呢。
那女的背对着我,我一时倒不知道是谁。我缓缓走过去,打了声招呼:“妈,家里来客人了?”
老太太抬眸看我一眼,一向不拿正眼瞅我的眸子里居然闪过一丝慌乱。于是我更加好奇,恰巧那女的也转过头,下一瞬间,我们都从彼此的眼睛里读到惊讶。
夏云说我跟她长得像,倒也不全是。面前的女人个子比我高一点,胸比我大点,头发比我长点,皮肤比我白点,声音也比我媚点。真不是我谦虚,怎么看人家都要比我好点。要是林越深娶我真是因为这个女人,那我还真替林越深感到委屈。我这个翻版跟正版一比,怎么看也只能算个残次品。估计我唯一的优势就是年龄比她小点了,这一条还是我猜的。
“夏果是吧?我早就听说过了,没想到今天才见面。你好,我是陆蔓。”陆蔓站起来,高挑的身材一下子就把我压下去一截。她伸出藕臂,大大方方地跟我握手。
早就听说?听谁说的?为什么我是到今天才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
我微微一笑,将手伸出去同她交握。有老太太在,我自然也得大方得体些,不能太过失态。
“咳。”老太太咳嗽了一声,将咖啡杯搁在茶几上,又瞅了一眼我被纱布包裹的手指,“坐下吧。手怎么了,给我瞧瞧。”声音里居然还带着那么一股宠溺的味道。
得,老太太又开演了,我得扮个乖媳妇。
我自然地走过去,在老太太身边坐下:“就是被玻璃扎了一下,不疼的,妈,您别担心。”
“瞧瞧我这个媳妇儿,成天跟个孩子似的把自己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了。我没养过女儿,现在全当多养一个闺女了。”老太太握着我的手指,笑呵呵地对着陆蔓说。我看见陆蔓的脸色变了变,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优雅地重新落座。
我被老太太一番话刺激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心想:老太太,您演得太过了,会穿帮的!
“对了,小果,陆蔓刚回国,对国内还不怎么适应,想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你看呢?”老太太侧头温和地问我的意见,眼神却暗含警告。
得,这家什么时候轮到我做主了?您都答应了,还问我干什么?
我说:“行啊!待会儿我让用人收拾一间客房出来。陆小姐,您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我好跟用人说。”我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太太暗中掐了一把。我立马反应过来,估计我会错老太太的意了,老太太是想我拒绝来着。
我太委屈了,依您的段数都不好拒绝的人,我怎么可能拒绝得了?老太太,您太高估我了。
“讲究倒是没有,夏小姐,你太客气了。”陆蔓手执好看的瓷杯抿了一口,漂亮的眼睛微微一眯,估计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老太太暗中横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语重心长地跟陆蔓说:“蔓蔓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国外不比国内,离婚算不得什么的。有好的,伯母亲自帮你留意着。你也是,好好的,怎么就离了呢?要是换了越深,我才不这么由着他!夫妻两个能走到一起,实在是不容易,怎么能说离就离?”
我下午吃的鱼差点全吐出来。我还记得我跟林越深刚结婚那会儿,老太太天天让林越深跟我离婚,成天叨叨着趁媒体还没听到风声,得快点离、赶紧离。后来媒体一曝光,老太太估计觉得林越深不太可能跟我离婚,这才消停了。
陆蔓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特别难看了,脸蛋儿惨白惨白的。不过她还是忍住了,甚至还朝老太太笑了笑,礼貌地说了声“谢谢”。我想,这女人的心理素质太好了。当年我第一次跟老太太见面的时候,恨不得拿根针将这老太太的嘴缝上。
晚餐的时候大家用餐很安静,家里的规矩一向是食不言、寝不语。老太太坐在首座,林越深和陆蔓坐我对面,夏雨坐我旁边。估计下午吃多了酸菜鱼,我没什么胃口,只帮着夏雨切牛排,自己倒没怎么动。
陆蔓刚好坐在我对面,用餐十分优雅,举手投足间跟老太太有点像,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这是个吃东西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女人,是被夏云称作我下半辈子最大的噩梦的女人。我突然觉得这个场面有点滑稽。
估计我看人看呆了,挺不礼貌的,林越深警告地瞥了我一眼,我忙转移了视线。不久后,就见林越深将我面前的餐盘拿过去,把盘子里的牛排切成小块,然后才重新递给我,动作行云流水。我又呆了。
我想起夏云说:“林越深最近是不是对你特别好啊?估计他是想气气她。”
我愤愤地把牛排塞进嘴里,想着:这女人可真是不好对付,我不仅得陪着老太太演戏,现在还要陪着林越深演戏,我容易吗我?
林越深就是脑子有病,好好地等着人离婚不就行了,找什么替代品?折腾!
我想得太投入了,压根忘了嘴里还有一块牛肉,所以一下子就噎着了。我一只手捂着嘴拼命地咳,一只手去找水,摸到的高脚杯里全是红酒,却被我当成白开水一口全灌了下去,结果,酒精的味道更让人难受,我不得不拿了餐巾跑到外边拼命地咳。
我以后再也不敢说林越深的坏话了,报应来得忒快了!我一边死命地咳着,一边心有余悸地想。
结果,我一抬头就看见林越深追出来,递了一杯水给我。他微微皱着眉头,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换我我也不高兴,难得帮人切次牛排,还把人噎着了,这戏演得太不到位了。
我冲他讨好地笑了笑,没说话,可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抱着手臂凉凉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大步走回餐厅。
这时,陆蔓已经放下手中的刀叉,她拿着餐巾纸擦了擦嘴,然后微笑道:“我吃完了,你们慢用。”说完后,她就起身离席。
从头到尾,别说对话了,两个人连一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要说没奸情,谁信啊?太做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