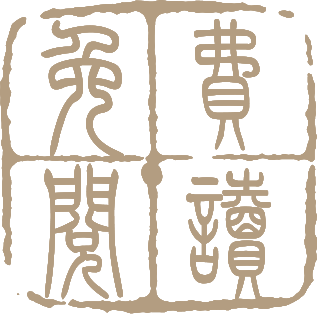
|第二回|
云溪僧风鉴识储君 月桂轩弟兄生口舌
却说指修和尚,与五台山云溪和尚并世齐名,云溪、指修都是蒙古喇嘛出身。尚来喇嘛僧都有法术,云溪在前清时候,曾替西太后祈病,故能宠膺锡命,住持五台山上。一般人信仰云溪,都说他能道过去未来之事,其实是一挑半剔之伎俩。谈言偶中,秃子的声名不觉得一日千里,王公贵胄争各徒步登山,叩问休咎,云溪的架子也一日大似一日了。云溪在京城内遍布耳目,但凡伟人勋爵,一念偶动,早已得知消息。
袁克定在帝制进行期内,深恐各方面反对,究不能十分把握。问知五台僧灵异,特地改换装饰扮做商人模样,欲问心中之事。及到五台,不免下与登山,五台的风景虽佳,克定也无心赏玩。进了山门,迤逦来至经堂,只见云溪高据法座之上,正与善男信女谈说休咎。
和尚两只贼眼,止不住在四下里轮瞧。忽在人丛内看见克定,急忙跳下坐住,嘻开一张弥勒佛笑口,合十起敬道:“贫僧天明入定之际,已知大贵人今日登山,故遣侍僧等在山门前迎候。今果福星莅止,不但是佛门的光辉,也是贫僧的缘法!此处人多杂乱,恐亵大贵人身体,请到方丈室屈坐!”
这和尚手甩念珠子,蟹行鸭步,光头皮一步一颠,把个大公子引至方丈室,忙叫佛奴等斟泡特别香茶,出出进进,狗头屁股似的好不忙碌。和尚一会又进方丈室,笑向公子道“大贵人且坐片刻,待贫僧应付众男女,再来谈叙。”说罢自去。
袁克定自想:我与这和尚素未谋面,如何他能在人丛内识我,且预知我光降?方才上山之顷,山门左右果有侍者等指导,可见是前知不昧了,若将心事叩问,必得正确之回答不觉心内暗喜。
公子在方丈室久等和尚不至,不觉得室中的字画反覆观看。字画看过,又看案上的陈列,佛书经卷之外,另有一册锦装的薄籍。克定疑是缘簿,抽出一看,只见签条上写“禅门日记”四小字,翻看前数页,有些如谣如谚的谶语,与烧饼歌仿佛。克定看了半日,十中一二,仿佛可解,又可惜首尾颠倒,不成片段。又有甲子乙丑等许多细字,注于歌谣之下。克定不觉叹异,怱怱翻下,后面都是日记。看至最后一条,上写某日某时,袁贵人来寺某月某日注数语。
克定正看得诧异,只听得走廊下履声橐橐,和尚已至。急把日记掩了,置于原处。云溪进门合十道:“适才遣谢俗客,免扰贵人车驾,只恐招待不周,多有得罪耳。”
克定道:“大和尚何以知下走要来此处?”
和尚呵呵大笑道:“试问大贵人,何以知道贫僧?大贵人既要来看贫僧,贫僧自然知道。贫僧的心,就是大贵人的心,心心合一,有感斯通,就是这个道理了!”
克定道:“上人既有前知,可知下走此来,所为何事?”
和尚呵呵大笑道:“大贵人远道而来,一不是谈禅,而不是随喜,不问人事问天意,不问终身问万年,天机不可泄露。然而未来的天机,已被大贵人看得明明白白了,问所问而来,正不妨见所见而去。”
克定听至此处,又不觉心中一怔道:“下走混迹清府,偷看日记,实系不合。但恨钝根人不能领会,还求上人指教!”
和尚又笑道:“未来之事,如一把乱线,无从说起。今有八句偈语,待贫僧念下,大贵人记取就可明白数分了。”就合掌念道:
老龙翻身,小龙攀鳞。
八百诸侯,大会孟津。
一人有道,四海归化。
皇天无亲,惟德是亲。
和尚念着,克定拿起一枝笔赶快书。写罢搁笔,克定尚要问话,和尚道:“偈语分明,居士与贫僧再有问答,俱成蛇足了。”
只有努力进行四个字,是当头棒喝。克定克欢喜,而回宫见父,说明此事,父子二人都道金銮殿牢稳可坐了。克定后来暗想:老龙是他父亲,小龙必说自己了,小龙攀鳞,系自己将来由太子而做皇帝。继而一想:诸弟中二弟克文,虽则言谈宗旨与自己不合,然他是一个文人,且淡于名利,当然不怕什么。只有四弟克端,是第三姬何氏所出,为人静穆颇有机械之心。他父亲宠爱何氏,故也钟爱克端胜于诸子。
克定恐将来有废长立爱之事,所以帝制筹备虽尚渺渺茫茫毫无把握,他已处心积虑暗中收养死士,比于门下的食客,出入护从,有百余人之众。又叫人散布言语,说克端如何浪荡不务正事,终究是庶出之子,不像载福之相。克端也知克定之用意,甚至兄弟见面,一言不发。那克定又摆出长兄的身分,时事呵叱。
克定一日从福禄居出外,只见他四弟向身子边走过,昂头上视,一言不发。克定把右脚重踯,叫克端名字道:“你岂不闻兄友弟恭的古训?岂可见长兄全无礼貌!我告诉老爷子,将家法处你!”
克端冷笑道:“做兄的先自不友,做弟的如何克恭?”
克定大怒道:“放屁胡说!试问我有甚不友的证据?你不恭之状已是彰明较著了,况且兄即不友,弟不能不恭!譬如做父的虽则不慈,为子的不能不孝!”
克端又冷笑道:“人类平等,世界共和,就是家庭间友恭慈孝,也须对待并举。可笑!你未做太子,已蓄养死士,效胤禛的故事!老实对你说罢,父亲未死,我尚在荫蔽之下,煮豆燃萁的手段,用得太早哩!”
克端一路说话,已匆匆而去。克定大怒道:“你说的什么野话!我与你见老爷子去,打你这一个野种!”
克端一听“野种”二字,无名火顿高十丈,回头请问道:“什么是野种?”翻身就递一个巴掌,无如克端矮小,打不着克定。克定要抓克端,又向前逃走了。两个人叫骂追赶不觉已至月桂轩窗门外。
原来月桂轩,就是袁世凯秘密办事处的后室,为袁氏特别起坐处。每到公事歇手约略休息之时,袁氏一个人必来此处,众妾乘此必然连翩入室列坐谈笑,各显自己的神通,献媚争怜,与这老奸雄解闷,天天如此,习为故事。袁氏因藉此,可以调和各人的情意,一日之间,无彼此隔阂之弊,免得羊车不至,望穿秋水。
袁氏这几天,因干儿子某某及远房侄儿某某等,替袁氏奔走四处,游说军阀,颇有几分眉目,正与众妾谈论将来帝制实行,如何尊显荣华,一派满心满意的梦话。
洪氏凑趣道:“老爷子该做皇帝,星相卜士,哪一个不如此说!可是天命所归,天大的福气,推也是推不出,古书上说‘有大德者,必得大位’,又道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如今淮泗等处,麦秀两歧,浙江山里出了一只凤凰。许多故事还不打紧,听说项城祖坟上,几日工夫生了一支血藤,粗若儿臂,其赤如血,宛似一条真龙!”
洪妃的话未说完,袁氏忽然变色,恶狠狠盯了洪妃数眼,洪妃尚未觉得。三姨太素忌洪妃跋扈,今见袁氏蕴怒,心中大喜,紧握四姨之手,暗中示意。原来洪妃处处招惹他人且与袁克定连络往还,不拘形迹,因洪妃最得袁氏宠信,克定为活动帝政起见,不能不用些手段,袁氏偶尔撞见已很疑忌,况填上血藤之事,是据家乡人信上说起。克定方来报告袁氏,尚叫他暂守秘密,转瞬之间已被洪氏得知,袁氏岂不恼怒。
袁氏方在恼怒,三姨正在得意,正待想句刻薄话儿奚落三姨,不防窗外面大闹起来,只听得窗外道:“我打你这阴险刻薄、跋扈不臣的东西!”
三姨听得是克定的声口,又听那一个道:“我有老爷子在上,不配你打!更不须向候补太子称臣道僕!你骂我野种,是何道理?”
袁氏一听克定的口气,心中有触,不觉无名火增高十丈,隔窗呵骂道:“两个人干什么?四儿,走进来!”
克端走入,立于三姨之膝下,克定跟随而入。袁氏骂道:“我未做皇帝,你已摆尽大阿哥的架子了!安见得我正位之后,就将青宫付你?安知我他日,一定立长不立爱?你有甚靠傍,想得这样稳当呢?我知你这几天,在外面七穿八跳很不安稳!”说此话,又拿两只肉眼恶狠狠盯了洪氏几眼,吓得洪氏面似金黄,樱桃嘴上全无一点血色,牙齿尽皆干燥。
克定更惮老子的神威,急将帽子脱去,跪于地上磕头认过。袁氏稍觉回心,即道:“四儿过来!”
四儿走过,袁氏执手道:“你须潜心学问,不要学你哥哥,专一生惹是非!”克端唯唯。从此克定做人,敛迹了许多。
其实袁家诸子,只有第二子克文,字豹岑,别号抱存,又号寒云主人,系二姨太所出,情性最为淡泊,胸襟潇洒,文学优长,与京内外文人学士诗酒之会,殆无虚夕,看得荣华富贵,不在心内。
今见六君子十三太保筹备帝制,轰轰烈烈,仰天叹道:“国家大计定以百年,朝三暮四,狐握兔埋,成什么说话呢?可叹这一班书呆子,有文无行,不顾天下人痛骂,本不足惜。然而父亲的英名被他带累,一朝失足,补救已迟,倘若知而不谏,就不算人子了!”
克文从此,屡此乘机谏阻。无如袁氏雄才大略,大有席卷天下,囊括宇内,取之一旦传之万世之志,听克文谏阻之言,只当是死守简编的书呆子,不足与闻大事。每将诙谐之语,应付忠言。克文因谏言不用,十分懊闷。
回到室内,却值袁氏的次女淑顺与克文爱妾秦玉琴问话,彼此叫应谈话。且说淑顺是三姨太所出,嫁与贵州巡抚沈某做儿媳,及沈家父子双亡,淑顺每年回京省父,后因往返不便常住袁家。这淑顺贤达知书,操持家政有条不紊,在兄弟中与克文最契,故时常来往。
今见克文谈话,颇有牢骚不快之意,问知底细,克文从头细说,重又叹道:“一班书呆子!扰乱国政,全不想国内的民气如何激昂,外交界的责言,如何严厉!这万恶的京华我不能一日再居了,快快儿跳出是非圈,图一个清净!万一事情闹大,我只好披发入山,管不了许多闲帐!”
淑顺闻言,也甚嗟叹道:“二弟出京远去,免与大哥争执,也是善计。老爷子一时性执,待做妹子的聊尽一番几谏,若使无效,也只好辞别父母,遄归老家去了。”
克文点首道:“二妹肯如此存心,阿兄得宽了几分儿责任!大概妇女之言,较为婉转,或者日久时长,老爷子能回心转意,妹子就是旋转乾坤的大功臣了!”
克文当日,约略检点行装,挈眷离京,做云游四海的神仙眷属去了。暂且按下。
此时袁世凯,筹备帝制,用着那一班心腹爪牙,借外债,提中交两行的基金,提国民捐,设立筹安会,制造民意,收买异己暗杀志士,筹备大典,把盈千累万的金钱取之尽锱铢,用之若泥沙,全不想小百姓将来血枯汗竭,如何担负得起。就是府中费用,比在彰德之时增加不啻倍屣,正供不计之外,大家还落小货,仿佛袁世凯金銮殿已经坐上,万方环賮,尽输天府似的。幸有淑顺在内,不避嫌怨,把府中的用度划分得井井有条,剔除縻费立一个每月预算表,不致于偏枯紊乱。袁氏大为称赏,就是于夫人也说她做事不错。
袁氏一日公毕,与儿媳等说家常话儿,不觉提及帝制,又道:“克文不别而去,今无音信,其实可恨!”淑顺微言解释,随劝袁氏把事情看破些,说父亲年已望六了,天大的富贵无非传与儿孙。然而太子只有一个,兄弟却有十数人,无论传与哪个,终有争执,宫闱喋血之祸,终不能免。何苦外失人心,内召祸乱呢!
袁氏不料此女有这番说话,虽要驳斥,苦于无从驳斥,假意叹道:“我何尝要串这一出巴戏!奈为民意所迫,未可峻拒!”
淑顺道:“平心而论,无论中外人民,未有不爱共和而厌专制的,所谓民意,也只是少数的民意,被金钱势力驱迫而成。父亲自入政界,威名震于中外,令名永保,何患不做终身总统!二三宵小妄想攀龙附凤,做就圈套朦蔽父亲,何苦一世英雄,做他人的傀儡呢?”
看官听说,淑顺一番婉谏,句句是金玉良言,无如袁世凯把“皇帝”两字迷了心窍,虽有忠言等于逆耳,总是唯唯不决。淑顺苦谏数次,毫无成效,袁世凯此后凡关于帝制的一应事务,在于夫人与淑顺面前一字也不泄漏。并且克定事后访知淑顺进谏之事,心中大怒道:何物女子,妄干国政!此风一长,以后还可做事吗?
其实克定,记着宫闱喋血之语,恨她出言过火,于是授意府中的姬妾仆婢,事事与淑顺为难,百方挑剔。原来府内男女,向来怕惧克定,号令一出,唯唯遵行。淑顺顷刻之间四面受挤起来,责言纷至,怨声不绝,帐簿表册无端缺少,甚至贴身丫头也在暗中弄鬼,洪氏柳氏又在暗中下石。
淑顺叹道:“我言不用,此间不可更居了!”含着一包眼泪,走别于夫人。
于夫人道:“我儿为人端重,虽非我所生养,但与你性情契合,不异所生,自你到府之后,省我操心不少。恨我这个逆子不能容你,老子也不顾你在此,我也不愿久在是非圈子里!你先回湖南沈家去罢,等我回彰德之后,再来接你回住。”
两人执手,想到前路茫茫,止不住四行眼泪如搓绳挂线一样,绵绵不断。反是淑顺强笑,十分安慰于氏。淑顺又别父亲和三姨家人等,大家也不很留,行李萧条,黯然出府而去时方秋始,木叶微脱,蝉声载途,一路行程,更兼别母离爷,止不住苍凉之感。女士在府本已积劳,况路上寒暑不均,一至汉皋已是病莫能兴,只得旅馆住下,一夜功夫病情加重延医无效,客死旅馆。只有一仆一婢相陪,临死之际尚呼父母,可谓伤心之极了。有人议论,女士死得可疑,做书的无形根据,不敢妄参末议。正是:
巾帼几人知大义,汉江呜咽吊湘灵。
要知后事如何,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