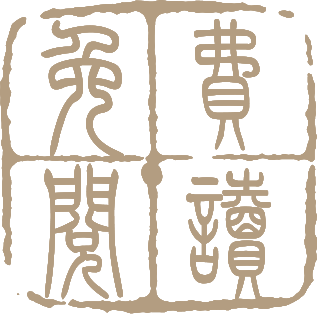
|第四回|
霹雳一声天崩地坼 缇骑四出鬼哭神号
却说袁不同在公园内看小说,等待龙女士。正在寂静之际,忽听有人叫唤,回头一看却是一位少年,西装打扮。原来是自家好友刘蔼南。
蔼南一见,拱手道:“恭喜袁兄!老伯已升大典筹备处处长了。君家大皇帝,早晚践位,老伯论功封王,吾兄也是世爵的王爵,从此之后,可把同志同党一个个拿来消遣。”
不同不等蔼南说完,沉下面孔道:“你少挖苦些罢!你既是疑惑兄弟,还是离开远些儿,免得危险!”
蔼南道:“我说笑话呢!薰莸不同器,莫非你兄弟不知道?”
不同道:“闲言少叙。我们的事体进行如何了?”
蔼南叹道:“辇毂之下,其实难做事!”
两个人说话未了,只觉紫藤花外,有个人影儿在眼中一闪,两人的说话就低了。不同抬眼,正见龙女士穿一身白秋罗衣服,斜倚石阑,一手掠鬓,抬眼看不同,似有些忧怨之色。大概因不同另约朋友,不能与她谈话,不无抱怨似的。不同正要起迎,已见龙女士分花拂柳,绕过石阑,袅婷婷徐行自去了。
不同与蔼南说罢,假称小遣,从假山后面抄取小径,走上石磴,与龙女士在小蓬壶阁内相遇。女士嗔怪不同,为什么另约他人谈话。不同分辨道:“昔日的朋友刘蔼南,不期在此间相遇,不能与她招呼。况且他是我铁血会同志,也是世家之子,热心做事,可托肝胆。”
女士点首道:“我叫你来,商议目前的大事。我想袁氏此刻未登宝位,人心未尽归附,必须如此作弄一番,事成之后,灭了这位魔王,与天下人吐气。事若不成,也足以褫奸雄之魄。然而此事,只有借重君父做一个傀儡,至于后来之事,我在宫内自能调度。”
不同大喜道:“卿有此志,我必一力成全二人!”
议彀多时,方才走散。却说不同之父,一日从宫内回家,只见退闲室内花架上,摆了四盆月季,叶肥枝矮,花似金盤,问不同道:“此花何来?”
不同说:“儿游白云观,经过一处花园,见有此花,非但种子特别,并且绿花绿叶颜色奇异,为花谱中第一贵品,故出重价购买。细看花朵之上,现出淡白字迹,各盆都有,像‘一’字的,有像‘山’字的,惜不能辨得仔细。”
其父不信,近花细看,忽然惊叫道:“这不是一个‘江’字吗?”又指一盆道:“这一盆花,好像一个‘统’字,拼拢来说,是‘一统江山’四个字!可见今上登极,乃是天命有归,所以草木山川,无不效顺。方才我在宫内,听说山西一个山内,发现石龙形迹,祯祥迭著,不是偶然适合了!明天可把这花儿送往宫内,叫今上欢喜!”
不同急道:“儿买此花,园丁再三嘱咐,他下种之时盆底放置硫磺物质药品,切不可换盆另种,倘憎花盆不合,可加套盆在外。”
其父道:“我知道了。”
至第二日,果把四盆花送往新华宫内。袁氏看见花朵上,字迹分明,确系天与人归之兆,龙心大喜,即置于福禄居走廊之下。正于这晚上,袁世凯的干儿子某氏入宫请见。原来这干儿子,在前清时候,本为某爵相的家奴,招权纳贿,无事不做,后因事败被逐。因已腰缠丰富,就出些造孽钱,捐报一个同知,在直隶省随班听鼓,数年奔走,未有差委。
彼时袁世凯正做北洋大臣,与某当道十分倚重,彼乃一面走某当道的门路,一面另具厚礼,拜于某大胡子门下。这某大胡子本与袁氏世交,袁氏贫乏时,某大胡子有通财之谊肝胆相视,十分投契,及做练兵大臣,派某大胡子做全军参赞。
袁氏因某大胡子诙谐得趣,常与他私下游玩花丛。袁氏曾在韩家班妓院内,与名妓柳三儿啮臂深盟,情逾胶漆,只因他身为大臣,不便在任上公然纳宠。某大胡子窥见此隐,因某氏求他提携,就把锦囊妙计授与某氏。某氏假称商人,自往韩家班,混与柳三儿结识花费一笔重金,替三儿脱藉,另租华屋买办全堂器用,把柳三儿迎了过来。
某大胡子假约袁氏访艳,径来宅内饮酒,及至夜深酒醉,三儿出来斟酒,盈盈下拜,袁氏大惊,某大胡子笑道:“今天是吉日良辰,不宜孤负。”就把袁柳二人送入洞房。
袁氏惊问底蕴,方知是某氏用的一片好心,袁氏大喜道:“某某人孝顺如此,真好儿子也!”
某氏在旁,被某大胡子一推道:“还不替干爷干娘叩喜呢?”
福至心灵,赶即跪至地上,磕了数个响头,口称“义父提拔”。
这是某氏拜为干儿子的原因。从此某氏见了世凯,不称义父,即称父亲。民国初间,称为总统爷爷,帝制时代竟称父皇了,非但在袁氏处小心献媚,甚至六宫嫔御,无不满打招呼,房中贿赂输送不绝。袁氏自然把某氏,看做第一个心腹,放在边省做一个将军。
所有袁氏制造民意,某氏十分出力,一日间往来的电报,不止一二十通。这一日,时已向夜,袁氏在秘密办事室,批阅各省将军等来电。忽问这干儿,自来请见,儿心中默念道:“他与我数天不通电报了,正怪他疏懒,今日自来必有要事。”思想未毕,某氏已入办事室,请安叩首,行礼已毕。
袁氏叫他坐下,道:“现在西北省分,颇有反对之声,你须在彼处坐镇,侦查异议之人,何得轻离本位,授人间隙!”
某氏道:“父皇高拱九重,近有腹心之患,非同癣疥之疾,臣儿不安寝处已数日矣,诚恐通电奏奉,易泄机密,故星驰电掣而来。”
袁氏惊异道:“你说腹心之疾,究指哪个?我一点儿不知道。”
某氏道:“父皇试想,如今父皇身边最信托者,何人?”
袁氏道:“我生平一秉大公,在我处做事的无不信托,你的言语尚未明白。”
某氏道:“就是新拜处长的假皇族,他要大义灭亲,闹什么政治革命呢!”
袁氏干笑道:“你的神经也太敏捷了!是袁某吗?他其实忠心于我,我将他一手提拔,有此地位,况且大典筹备处是一个赚钱的好缺,我有心挑发他,他有人心,难道不知感激甘与自己倒蛋吗?总之是彼此排挤,人言不可尽信。”说到此处,把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履看某氏。
某氏道:“臣子不敢妄报,因袁某的儿子袁瑛,驰书各省军官,反对帝制。他并有一信,致于奉天某将军,彼因不敢隐秘,故把此信叫臣儿转奏。”说时呈上书信。
袁氏一看此信,果然信内措词十分激烈。袁氏把一张面孔气得铁青也似,几根银丝鬓四张如戟,某氏道:“还有运动模范团的血书,尤属荒谬!”
袁氏怒极啮齿,冷笑道:“荷叶包刺菱儿,里戳出还得了呢!”道言未毕,忽听宫苑内一声震响,如天崩地裂一样,殿宇震动,梁尘下落,电灯也半熄了。
这一位身经百战,心雄万夫的大奸雄,也不免变色张皇,急攫案上的手枪,躲至保险室去了。原来这保险室,系在秘密办公室之后,系四方一间小室,铁板为墙,四圈都叠沙袋,有两重电气铁门,按其机关,一手可移,不得诀,门万夫莫动。是一位德国工程师承造的,以防反对党起事,可以入室藏身。并且,此室下有地道,曲折周行,可出宫外,而且铁门一闭,地道中电灯顷刻生辉。据说俄皇宫中,也有照样的保险室,也是此人承造。
闻言慢絮,却表大声起时,可怜宫内外许多男女侍从、官模范团、拱卫军等,各吓得露尾藏头,战兢不迭。过了多时,别无动静,方才一个个出头打听。一时宫禁内,电铃的声音,“的令令、的令令”,声震不绝,问来问去,一些底蕴不知道。
袁皇帝惊定之后,怒容满面,立召侍从女长严令查勘。查至福禄居转角,方见门坍壁倒,有一个半炸的女官,仆于地上,尚见后半个身子,蛮靴配剑,前半身已不知去向,花盆架已少了一个。
女官长据实还奏,袁氏沉吟道:“必是那乱臣贼子,从中作怪!”吩咐侍从女官长,速把未炸的花盆慎重取下,细心检视。女官长承命检查,果然其余三个花盆泥土内,掏出铁罐头三枚,封闭严密,十分沉重,不是炸弹是什么呢?大家思考此事,必是花盆内预藏炸弹,待举大事,侍从女官不知底蕴,误触盆架,以致死于非命。
袁氏得奏,即并派心腹侍从,互搜宫内嫔妃、女官众人的卧室,翻箱倒筐,破壁移砖,扰乱张皇,一言难尽。移时天明,袁氏即密召袁某人入宫,袁某上晚正为筹备大典忙碌,上床已迟,今问主上侵晓见召,十分匆促,不知所为何事。只得胡乱盥沐,吃些干点入宫两足软绵,心内迷糊。
君臣相见已毕,只见袁氏冷笑道:“你家贵公子难得有此盛意,送这个花草儿,幸而破案的早,昨夜里有人替死了!试问他安心毁我,他有什么好处呢?你且与我说明此花的来历,否则你与他必成一党哩!”
袁某听袁世凯埋怨,一句话也不懂,料想上了小孩子的当,酿成命案非同小可,只顾跪在地下,碰头哭辨道:“微臣愚昧,不知何事取罪!但求明降圣谕,臣虽万死不恨!”
袁世凯此刻,忽然怒气渐消,叹一口气道:“你已跟我数十年了,我知你已久,谅不至于胡闹。但你这孩子,不知安的是甚心,竟把你做傀儡,出此奇案!”说到这里,就把昨夜宫内震动,及花盆内搜出炸弹之事告知。
袁某吓出一身冷汗,口噤不语。
世凯道:“从前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清延不予严办,可见革命党终不能免,但你儿子年轻,不能把事情想得如此周到,暗幕里必另有别人之使,图一个里应外合。你若能根究出主使之人,其余附从的,可以概置不问!”
袁某唯唯退出,一路还家,直气得三尸神爆跳,七窍内生烟儿。见他儿子,不问是非,先是隔头隔脸一顿臭打,叫家人捆绑了,泪流满面,气哄哄说道:“我巴结主子,得有今日,不是容易之事!咳如今养虎在家,要送我老命了!”
不同尚要强辨,袁某就把事情始末说出,逼问他儿子,这四盆奇花何处所得。不同叹道:“父亲既受主知,若能乘机规劝,使袁氏不为非法皇帝,就是第一清贤豪了!只因父亲醉心于目前的富贵,不顾天下后世的非难!儿子不幸,读了几行书,又灌输外国最新的学说,不觉与父亲的宗旨各走极端。所谓国而忘家,各行其是。儿虽不孝,然而对于民国不可谓非忠臣了!”
袁某大怒道:“你已不忠不孝达于极处,还有什么巧辨!我惜老命,不能擅把乱臣贼子收容取罪,只有把你送至步军统领处,问供定罪,丝毫不容袒护了!”因叫一声“人来”,把个袁不同抬上汽车,押至步军统领江朝宗那边去了。
原来,袁不同四盆奇花,是药水薰制,蒙蔽了许多人眼目,正自好笑。袁某押儿子进了统领衙门,见了朝宗,密谈一切,请他督禁逆子,今上必有后命。拱手退出,回至寓所忽问袁氏,一叠派人召见。袁某命驾入宫,问:“袁瑛现在何处?此事不必深求,务须从速消弭!”
袁某内心一呆,嗫嚅应道:“臣已将逆子送往统领衙门了,听凭公断定罪。”
袁世凯眉头一皱道:“你为什么这般性子急呢?”隔了一息,又说道:“幸而江朝宗不是外人,不然又要闹什么笑话!你快出去,打听打听外边的风声,我再招呼他问罢!”
袁某站起来,领旨出宫。这里袁氏即打电话给朝宗,说袁瑛如何运动军队,及暗运炸弹之事,为他好生研询,穷究主使之人,倘若问出真供,即可派兵捕逮,送交执法处,先办后禀准有重赏。但这事一须秘密,二须火速,不可有误。
朝宗唯唯领旨,好不有兴。于是把袁瑛引至一间密室内,叫他从容坐下,先用一派哄吓之话,责他冒昧做事,害中家庭,祸延生父,又将总统的意旨说了,叫他供出指使之人余均免究,旁敲侧击,大有诱使尽言之意。且说袁不同自入樊笼,早把死生二字置于度外,心想一个人做事,何须有人指使。今见江朝宗得了自己,如得活宝一样,必要他供出主使。又道:“足下若守秘密,莫怪兄弟无情!这里有几种现成的刑具,是讯亡命刺客所用,十分结实,恐防足下娇养,尝不过这个味儿,故此优礼相加,不敢冒昧。若足下一味推诿,兄弟难以复命,只可对不住足下了!”
不同呵呵冷笑道:“大丈夫既做此事,早办一死,千焚五毒已看得如家常便饭一样,何足惧哉!横竖我招与不招,总不离一死字。然而事涉宫闱,不是什么革命党有心反对,你知袁氏已安排做皇帝了,这太子一席,众人心里都知属于大公子。大公子也不作第二人想,其实立长立爱,仅有回旋之余地,除是大公子外,以何人最有希望?足下日观天颜,深知宫内细情,已可不言而喻了。我是袁家之人,应该关心袁家之事,大公子青宫未定,已经目无余子,我袁瑛第一个心中不服,如今里应外合,要扶助此人,毁了克定!”
不同说到“此人”两字,把三个指头相并上举。江朝宗听见这话,十分骇诧道:“原来如此吗?哦哦哦,他本是飞扬莽撞一类人,你说里应外合,还有哪个呢?”
不同道:“我劝你少问些长短罢!我们袁家之事,管你甚事!”
朝宗道:“好兄弟,你若说明了,我好据情转奏,请旨定夺。谅这件大案子,自有顶缸的人,你倒可以脱身事外呢。”
朝宗也举三个指头道:“你说他吗?里头也须有心腹,方可于中取事,究竟与他同党的是那一起人呢?”
袁不同扯了一派谎话,江朝宗信以为真,耸耳侧目,点头叹息,做出许多怪相。不同不觉好笑,心想我索性骗他到底,假意沉吟道:“我为人做事须守秘密,一番言语已超过界限了。我是待死之人,何苦再把地理图奉献呢?”
朝宗道:“已有圣旨在先,你若从头直叙,决不与你为难,兄弟可以身家相保。这些同党是哪个,你快些说呀!”
袁不同听至此处,假意推诿,自在壮内寻思,朝宗催促数四,不同说道:“那个同谋的,有交通次长麦信监,内史沈中宪。”
朝宗哦哦答应,口念二人名姓,急在怀中掏出日记簿,君飕飕然写下二人名氏,又道:“麦信监、沈中宪之外,又有哪个呢?”
不同道:“又有内史沈印铭、苏季武。”
朝宗把众人的名氏写毕,又问道:“还有呢?”
不同道:“还有与本案关系的,宫中几个女子,我也未便宣布。”
江朝宗沉吟道:“我看这几个人,算不了什么大人物,谅来黎段两个人,都不能免呢?”
不同笑道:“就这几个人,也够你交代了!”
道言未了,门上人来回道:“公府里送来犯人内尉句克明、内史沈中宪,叫这边研询!”
朝宗益发相信,于是停讯,仍把不同还系特别优待室,更把句克明收禁了。随即点派人马,面授方略,各人按照不同所供的地方,分别查抄去了。只可笑江朝宗听了袁不同的鬼话,把许多人连家属老小提了来,一堂一堂研询,一些儿不得眉目,更无丝毫凭证。
江朝宗眼见一场赫赫的功劳,与水中捞月相似,好不焦躁,暗中骂道:“我落了这小子的骗局了!”一时雷厉风行把一班人抓了来,可奈此等人都有官职,不是寻常小百姓可欺侮,牵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如何寻一个下台呢?如今说不得了,只可抱一个邻国为壑的宗旨,往军政执法处一送,不就完结吗?想定主意,就叫御者备车,带同袁瑛押向军政执法处而去。
且说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心里比江朝宗明白,朝宗四处拿人,连日研讯,已弄得满城风雨,都知皇宫内出了什么操戈同室的奇案,也有说小皇帝併了老皇帝了,也有说宗社党得手,迎宣统皇帝复辟了,奇谈怪论传闻不一。雷震春怪江朝宗小题大做,不会应变,今闻江朝宗请见,叫门上人回道:“已经出去了。”
朝宗不得主意,忿怒说道:“我预知你主人在此,故来相见!”
彼此哄闹。震春知躲不过,只好溜出后门,从前门走进。
朝宗一见欢喜,弯头作揖道:“这几天宫里出了大事哩!我把这个谋反的乱党交与阁下讯办,分兄弟一半儿责任!”
震春假意惊怪道:“有这大事?兄弟一些不知道!究竟乱党是哪一个呢?”
朝宗疑震春真个不知道,于是二人约至秘室坐下,把案情本末从头细说。
震春道:“可有主子的特旨呢?”
朝宗道:“虽没有特旨,然而这几个人,我已曾受密旨,老兄放手重办,若有后患,兄弟两个肩膀,可以担承得起!”
震春默然不答。正是:
邀功未遂株连计,分谤翻存嫁祸心。
要知后事如何,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