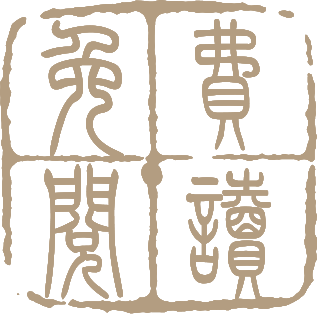
|第七回|
笔舌遭殃文人堕溷 金钱作恶政客戕身
却表袁世凯在临时总统的时代,国民党实力膨胀,人材如鲫。原来国民党,系留东革命党老同盟会改组,孙文、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都系国民党表表之人物,至于宋教仁学问见地更在诸人之上,一言一动党中奉若南针,尊为泰斗。
自从袁氏就职,孙文自愿让临时总统之席,专办全国铁路,黄兴自愿取消南京留守府,孙、黄二人先后进京,疏通南北领袖之意见,甘心贴伏,俯就袁氏之范围。一面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织内阁,施肇基长交通,陈其美长工商,熊希龄长财政,王宠惠长司法,蔡元培长教育,宋教仁长农林。
无如袁氏自揽行政大权之后,遇事独裁,以一人而综万机,将一座名流内阁弄得水冷冰清,形同虚设,用人行政都未得总理总长之同意。几位雄心勃勃的总长,天天吃老米饭睡晏觉,无事可做。唐总理一走,名流内阁纷纷解体,这一来,正合袁氏的心理,随任命袁氏心腹赵秉均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袁氏恐各省都督综握兵、财、政治一切权柄,未免尾大不掉,控制甚难,因倡军民分治之说。
湖北都督黎副总统首先同意,又把黎副总统诱致入京,另行派人继任鄂督,诱杀湖北军务司长张振武、将校团长方国维。袁氏又以南方军队的组织过于复杂,特派海军少将郑汝成会同江苏都督程德全,协办江苏裁兵事宜。其余各省,也都次第裁减民党的势力,逐步减缩。
原来袁氏操纵天下的英雄,不外数种方法。第一是金钱贿买,二是頭爵羈縻,三则笼络离间,使彼此同志之间互相猜忌,不期启衅而启衅,不期解体而解体。至于俊秀杰出的英雄,不为富贵所动,不为甘言巧计所中的,便以暗杀从事,或以卫生丸相敬,或以毒药潜贻,大都身死不明,冤沉海底。
非但对待武人如此,就是无关紧要的文人,若不能调转笔头儿替他歌功颂德,在辇毂之下,万不能苟全性命。在民国初年,曾有南京高师学校一位教授国文的老夫子,研钻故纸,薄有文名。他自执教鞭,盐荠白饭颇堪度日。
忽得北京朋友来信,再三教他入京,说总统敬仰他的文名,将加任用,千万从速一行。一连数信,说得这教习心思也活动了。暑假期内,专程入京会过朋友,先与他介见总理。总理代答总统之意,系叫他入教育部,编辑国民教科书,以鼓吹帝制为唯一宗旨,书成之后,决畀他次长之职作为酬报。
谁知这位先生,在文字上颇有些贞操,决不肯朝三暮四,随波逐流的,他就宛转辞谢道:“鄙人幼读几行书,年长之后又饫聆世界的政论,十年以来,心醉共和,主张革命,今幸帝政划除,江山光复,设若改变初衷,非但贻羞同志,及对自身也觉问心有愧,宁可辞贵居贱,营干旧日学究的生涯?”如此推三阻四,非止一日。
赵总理据覆袁氏,袁氏深为不悦道:“区区细事,你尚干不了,来麻烦我吗?他不做这事,怕没第二个人来做?但需给他些利害,不要出京之后,又仗什么报纸儿与我捣蛋!”赵总理碰了一钉子,默然退出。
过了一日,这一位教习先生坐了旅馆的车子出门游玩。行至一处狭仄的街道,前面来了几部车子,横都里又来一部马车,把教习的车子,只顾向后方推挤。拉车夫把车杆儿擎过头顶,把这位教习先生颠出车外,待叫“啊呀”之时,他的身子已落茅厕了。
原来旅馆的包车后面,没有铁撑子,停车适在茅厕旁边。北京的茅厕其深不测,与千人坑一样。包车夫见已肇事,急急拉车逃走。这先生浮沉在茅厕内大呼救命。直至车马通过,人声稍定,方才有登坑的听见,报告警察,把这位先生救起来。
原来这事体,并非包车夫偶然失误,系秉承当局的钧旨,大有“此辈清流,正应报之浊流”之意。秦始皇焚书坑儒,尚无此等酷虐。本以为失足深渊必无性命了,谁知被警察救起,累得这教习涤身漱口,易服薰香,忙碌半日。
正在懊闷之际,只见他的好友张皇来见道:“你做硬汉,可知好哩?这一场是非都是兄弟所害,你在此地不能再住了。我已替你买好南下的车票,急需速走,以免客死他乡!”
教习也恨得踯足道:“我一向安贫慕道,并不梦想干功名,贪图富贵。你害我狼狈如此,算是承你的栽培了!”
这朋友赶紧摇手,叫茶房收拾行李,悄悄儿说道:“茶房车夫,已被人买嘱了,说话须留神意。”即与他同往车站。
朋友又再三吩咐道:“此次南下,算是幸脱虎口。从此以后更需格外韬晦,万不可在笔头儿舌尖儿上逞什么风头,枉送余生!这是做朋友的忠告。你受了这一番教训,也可以知晓一二了。”须臾车开,二人分别。
以上所纪,乃是袁氏称帝前一段小小的趣事。常言道:“尝一勺而知沧海。”可见帝制党摧残善类,实属无微不至。这且不表,却说农林总长宋教仁。当南北相持不下时,宋氏奔走调和,其功不浅。后因唐总理辞职,宋氏连带下野,在上海组织《民权报》宣布政见,监督政府,扩张党势。国民党党员崇仰宋氏,不殊山斗,宋氏却能有功于党,所以组织参议院,召集正式国会时,国民党党员竟占三分之二。议案可否,几成一党专制之局。
原来老同盟会在外洋,同志本不甚多,及入民国改组国民党。老同盟派既握各部总长等一切权柄,新会员纷纷加入,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团体,加入国民党内,声势骤盛。
此外与国氏党对抗的,有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党并组共和党,又有第三党民立党,介居两大党之间。然而比较势力,终是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私心不足,眼见得孙文辞职,袁世凯独得现成天下,有组织内阁政党之提议。宋教仁把这个宗旨,在《民权》、《民立》等报上极端鼓吹。
赵总理有一日,在办事处阅报,心中忽忽不乐,撇下报纸,蹙额无言。忽有一个幕府,飘然而入。总理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现总统的小舅子、国务院秘书,姓洪名述祖,字荫之。他与袁氏,因妹子洪姨太的关系,十分亲信。洪述祖感恩知已,颇想建立不世的功业,回报衣食主人。
总理见他进来,即与他点首,请他坐下道:“足下想从公府里出来,可见过极峯吗?”
述祖摇手道:“主子这几天,性情焦躁,似变过一个人了,谁敢去见他?向老虎头上抓虱子!”
总理点首道:“你是出入上房的,必知他有甚不乐的原因。”
述祖笑道:“总理明见,无非国民字儿的嘘声浩大!就是总理也与布袋和尚一样,前后左右,六贼憧扰,如何能施展自如呢?”
赵总理听罢,也不禁冁然失笑道:“我何尝要做什么兴朝的首相?无非是极峯再四敦迫。我譬如一根烂木头,姑且把新建的大厦暂时支撑,等到栋梁齐备,这根烂木头当然无所用处!”
述祖道:“总理的存心,也忒谦退了!极峯以老友待总理,故以重任相托。大凡首相当国,必有旋乾转坤的功绩。今日政党嚣凌,南风不竞,极应操纵离合,消弭彼等声势。一则来无负极峯之信托,二则可把内阁的地盘渐臻稳固。大凡个人的出处,先须审慎。总理当日若不允登台,倒也罢了。既已出山,决不当苟且敷衍。总理的度量虽则宽大,然而民党的盛气却是难受。试思国会成立,国名党议员多至三分之二,议事未成,动不动弹劾政府,荆天棘地,尚有何事可做呢?”
洪氏一席话,说得赵总理悚然钦敬道:“足下忠告良言,足启聋聩!目下民党势盛,亦国家自然之运,岂能消弭得来?”
洪氏道:“鄙人有一计较,筹之已熟,如能采纳,必于国家有益。请摈左右,竭诚一谈。”
总理听说,果延洪氏入秘密室,退去左右,关门共坐。
洪氏道:“今南方所以猖獗者,以有三首领耳,一孙一黄一宋。然而孙尚空谈,黄无毅力。潜势力最伟大者,厥惟宋氏。此人脑力充足而活泼,见事明白,又富于中西学识,时在各机关报上发抒政见,大有独到之处,就是异党之人,也不能轻易非难。党中之人,更其仰若明星,籍为进退。况此人做事的手腕非常灵敏。前次入京,与极峯晋接,持论圆满,不落边际。只觉此人非金钱爵禄势力,所能羁縻得住。自唐总理辞职后,宋这农林总长不别先行,至次日,方得辞电。极峯顿足道:‘遁初一遁,天下从此多事了!’从此书空咄咄,有好多日,心中不快。这是内部消息,十分真确。试想这几时内阁的命运,风雨飘摇,国会的现象,强台竞上。按之内面文章,都是此人作怪。极峯的言,可谓明若观火了。”
洪氏说着,赵总理不住点首。洪氏又道:“现在彼党盛倡‘责任内阁,傀儡总统’之说,并推拥此公登台,倘成事实,岂非同盟会包办中国吗?”
赵总理手指案上的《民报》道:“责任内阁说,我已久有所闻。不图预备登台的,就是此公。依足下高见,有何消弭之策?”
洪氏道:“大凡急事急办,缓事缓办。彼等鼓吹进行不遗余力,自非急起直追不可。想彼等凭藉党势,以民意两字为标帜,文对武对,俱难若力。惟有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只须流血五步,伏尸一人,大事足了矣!至于孙黄在日,劣迹甚多,花些使费可以搜集证据,插图立说,流布国内,可以使二人声价扫地。失去彼党内中心人物,党势衰败,可翘足而待矣!”
赵总理欣喜道:“先生救国存心,匡时有志,诚今日之管乐也!但是博浪一椎,所关非细,安所得深沉大胆之武士,建立奇功?”
洪氏道:“现在南中,有一草庐歌啸之志士,手下敢死党,斗量车载。并且拥戴首领,永无侵叛。”
赵氏正色动问道:“这志士姓甚名谁?现居何处?”
洪氏道:“此人姓应名夔丞,字桂馨,家住上海,出身富厚。前清纳粟吏部,曾任江苏某县的知县,后因被劾落职。性喜交友,后入帮会,长江一带青红帮匪,尊他一人为首光复之际,曾入沪军都督府,充当侦缉科科长,因犯嫌疑停职,行文通缉。自此抑郁私居十分不乐。我与他相交日久,曾有金钱上往来之谊。他久思得当报国,图一官半职,荫子封妻,使党中人物也可提携一二,不致受人轻蔑。好在该党中好身手的健儿数多如鲫,能青天白日杀人于闹市之上,不留形迹;能于火车开行之际,乘势上落,轻若飞鸟。至于探囊取物,屈指藏句,游戏变化,尤其余事。总言一句,该党人才济济,真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兼收并蓄。极峯手内发纵指使的,并计十数人之众,然以手段与彼党中著名人物相较,犹在中下之列。若与姓应的商议,了却此事,真不费吹灰之力。”
总理点首道:“既然如此,你可先发密电,叫他包办此事。事成之后,可向极峯保荐大用,并得厚赏!”
洪氏摇首道:“我看此事决不如此简单容易的。一则姓应的此刻,尚系有罪在身,钻头不出;二则姓应的办事,虽不想急受赏赐,但是召集党羽侦伺宋某,必有种种贿买心腹运动交际之费,姓应的虽有家产,绝不肯事未成,先代政府垫款;三则姓应的要使人做事必须政府与他一个官职,叫应一切,方为灵捷。”
赵总理点首道:“所说姓应的,我也曾知一二,果是一个漂亮有用的人物。他果能成就大事,自有不次之赏。至于进行使费,当然源源供给。你先给个电报,叫他来京一趟,彼此会商一下子,方有眉目。”
述祖闻言,心中一跳,颇现踌躇之色。原来述祖献计时,本想从中提篮把秤,捞一笔意外之财。不料老奸刁滑的总理,偏要叫姓应的进京面洽,岂不是“戳穿西洋镜”——一钱不值呢!当下,蹙额摇首道:“此人在长江一带,踪迹无定。上海虽有住宅,亦不能知他住处。况我与他虽曾见面,未必脱熟,冒昧发电,反而落了痕迹,只好我自己向上海一行,与他当面谈判,较为稳便。他前在军队曾替张某某办事,不如请张某写一介绍信前去。”
赵总理道:“足下所言,可谓万全之计。好在张某现尚在京未去,我叫他写信。你明后天即可动身南下。”
述祖唯唯。数日之后,述祖果到上海。住下客寓,带同张某函件,坐了汽车,寻至文元坊应夔丞住宅。述祖相见已毕,取出张某函件。夔丞拆视,见上面写道:
“夔丞仁兄大鉴,敬启者。前上函电,计登签阁,每忆道范,时切神驰。京师自孙、黄诸公惠然而来,与大总握手言欢。社会之欢迎,日有数起,足为南北感情融洽之证,不胜为民国前途庆幸也。兹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所规划,当道盛倚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胜感企之至。弟如恒栗碌,乏善足陈。台从何日北上,函盼驾临,畅叙别情也。耑此敬请台安。弟张某某鞠躬。”
夔丞看罢来信,呵呵大笑道:“兄弟与老哥相知有素,用什么介绍信呢!”
述祖道:“私交自私交,公干自公干。因为谈判重大,兄弟人微责轻,不能担保老哥的未来富贵。所以另拉一个有力的居间人在内,使得老哥放心。”
夔丞道:“照此看来,又是极峯的主见了!主子在南中,死士众多,那些异党饮弹剸刃的,不知多少剑侠之盛,与清雍正时代大相仿佛,何必垂念兄弟呢?”
述祖笑道:“老哥一猜便透,足见高明!不过天下刺客有大小之分,以前所雇的江湖力士,无非是足下的鳞爪。至于沟壑捐躯的志士,也与国家全局无多关系。方今元首,安内攘外,旋乾转坤,把一座中华民国渐措于磐石之安。然而有一心腹之患,未能消弭,不在带甲的武夫,而在执笔之文士,足下可知道呢?”
夔丞呵呵大笑道:“元首所虑极是!此人的文章经济,确系高人数着,天下民党皆倚他为耳目。一言既出,众论佥同,似有催眠术一样。元首欲了此事,兄弟可以担承。但是一切条件,必须预订。”
述祖道:“这个自然。兄弟南来,正因许多事情,非大家面洽不可。”
二人谈谈说说,甚为有兴。夔丞就留述祖在府内吃饭,连住数日,方才议妥。后来述祖还京。民党伟人宋教仁,死于沪宁车南站。轩然大波,震惊中外。后来赵总理、洪述祖应夔丞,与案内牵涉武士英等,皆不得好死。洪宪皇帝在屋内称孤道寡,只有八十三日,也就一命呜呼。正是:
纷纷暗杀曾何事,地下相逢总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