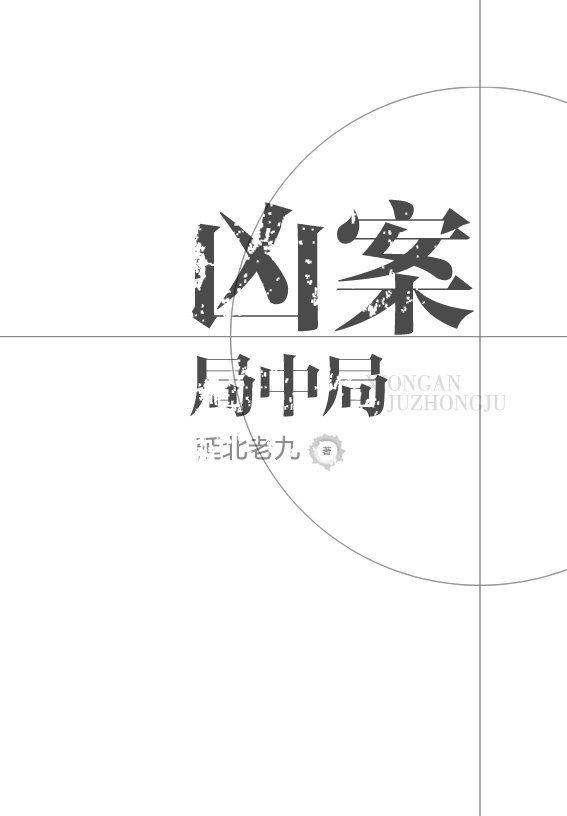
第二章 白衣嫌疑人
潘子可真绝,拿着弹簧刀扑上去,对着死人脸唰唰捅上了,嘴里还“你妈的、你妈的”胡骂起来。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潘子的弹簧刀刺到死人脸上时,嗤地一下全进入了,这要真是一张人脸,不管潘子用多大力道,一下也不会刺得这么深。我反应过来,心说难道是假的?我压着心口乱蹦的感觉,喊了一句,让他冷静冷静。潘子整个人有点木讷了,又刺了好几刀才反应过劲来,他看了看我,带着一丝警惕地对着这张死人脸摸了摸。正巧死人脸上有几个地方被戳出洞来,潘子就往这洞里抠了抠,等把手指伸出来时,还带出一截掺着棉花的稻草。
这竟是一个稻草人。我心里又纳闷上了,也凑过去,在这人脸附近摸索一番,还用刀把附近的灌木割断一些,腾出地方。等忙活一通后,稻草人整个身子显现在我俩面前。
它跟真人大小差不多,被木桩子斜着插在地上,尤其脸还故意往前探了一段距离,虽然上面早就全是窟窿了,但还冲着我俩诡笑。我知道,稻草人就是一种守护田地的人偶,防止鸟雀糟蹋粮食的,可这里就是灌木丛,灌木还比稻草人还高,摆个这么仿真的稻草人有什么意义呢?
潘子想的另外一个方面,他盯着稻草人,问我一句:“杜睿,你说刚才那笑声,会不会是这稻草人发出来的?”乍一听,潘子这话有点离谱,但我俩搜了这么久,也没发现啥人,只有眼前这个稻草人,难道真被潘子说中了?这稻草人里有什么古怪,能发出人的笑声?
我和潘子一同盯着稻草人的脸瞧起来。其实这稻草人在这期间还能笑一声的话,虽然挺诡异,但至少证明鬼笑是它发出来的,可我们等了好久,它就那么一直安静地站着。我知道我俩这么跟一个人偶耗是耗不起的,在没法子下,我又把目光转移,打量起它的全身。稻草人其他地方都好说,只是它的手有点怪,两个被稻草充的鼓胀胀的手掌都偏向一个方向,好像在做一些提示。
我们周围全是灌木,我顺着这方向看了看,根本看不清远处有啥,我一合计,心说难不成这稻草人是个路牌,它在告诉我们,那里有古怪?我把这猜测说给潘子听,潘子听完皱着眉,反问我:“那咱们是去看看,还是不去啊?”他这话说得很犹豫,说明他心里很纠结,我俩来到这里,按说逃过危险了,就该尽快回到土路上接着赶路才对,可之前的一系列经历都表明,这里不一般,甚至极有可能有我们需要的线索。我心说那就再抽出功夫瞧一瞧,把这里探个明白。
我表明态度,还叫潘子跟在我后面,我俩顺着稻草人指引的方向,继续开路。在齐膝盖深的灌木丛里走,特别地累腿,而在这种齐人高的灌木丛里行走时,我觉得浑身上下都累,就好像有个无形的手,一直捏我似的,让身上每一条肌肉都紧绷绷的。我和潘子就这么又往里走了一支烟的时间,突然的,在我扒开一片灌木时,又有一个怪脸探了出来。我刚有过类似经历,这次早有准备。我没让这脸贴过来,及时摊开手掌,一把扣在它脸上。
我缓缓神,又侧开身子,让潘子看了看这怪脸。潘子冷不丁脸色不咋好看,不过我俩都没说什么,反倒一同拿刀在怪脸附近清理起来。没多大功夫,我们就让这第二个稻草人现身了。看起来,它跟之前那个稻草人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它的双手指着另外一个方向,依旧是一片我们从没走过的灌木丛。我看这架势,心说得了,我俩大半夜的跟稻草人较上劲了。
我刚才一直开路,早就累了,这次潘子跟我换下位置,由他来当先锋。我心里默算着,我们在这灌木丛中一共遇到了四个稻草人,等按照最后稻草人指的路钻过去后,我们竟出了这片灌木丛。在灌木丛里我一直闻到的是一种略有发霉的烂草味,等走出的一刹那,吸到新鲜空气时,让我整个人都不由地一震,可当我往前一看时,这股振作的精神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面是一大片坟包,怎么说呢,这些坟包一看就不是一个时代的,有的荒废得都快塌了,有的干干净净,明显刚立没多久。这一片坟也悉悉率率的,零散地分布着,而就在一个新坟前,蹲着一个白衣女子,背对着我们,她手里抱着一个木盆,正从木盆里往外拿纸钱,在坟前烧祭。这大半夜的,坟地里蹲个她,我就算再怎么胆大,也一下害怕了,还立刻想到了女鬼。
我和潘子不由自主地往一起靠了靠,冷冷盯着那白衣女子看。这样熬了一会,那女子也不回头看我俩,更不说啥话,就好像我俩根本不存在一样。潘子忍不住了,又四下看了看,我俩脚下没啥小石子,却有拳头大的石头,潘子捡起一块石头,想抡圆劲丢出去,试探下这女子。正当这时,女子叹了口气,扭过头说话了,她问我俩:“你们是什么人!”
潘子要是真不管不顾把这石头抡出去,赶巧的话,真能砸在她脑袋上,甚至这一下子都能弄出人命来。潘子也没下那个狠手,他一看女子说话了,急忙一抖手腕,让这石头嗖地一下,跑偏飞开了。我没在意潘子是啥表情,全看着那女子,虽然离得不近,但我也能瞧出来,她长得挺清秀的,最明显的是眉间有一颗大黑痣。
女子看我俩不说话,又追问了一次,而且还笑了笑,那意思好像是打心里嘲笑我俩胆小。不能说我大男子主义,反正被她这笑法一弄,我心里来脾气了,心说管她是人是鬼呢,再咋滴她也是个小娘们,我俩就被这么吓住,太没面子。我还怕她听不清我说话,故意清了清嗓子,说我俩从乌州市来的,被上面安排到绥远村做实习老师。
那女子听完更来了兴趣,接着问我:“那你们有介绍信么?”要不是她看着太诡异,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在居委会工作的,怎么查户口呢?我和潘子头次来这种荒郊野外,如果能找个人问问,也能少走点冤枉路,虽然不想给她看介绍信,不过为了能跟她接上话,我只好忍了,一摸背包,把介绍信拿出来,拽着潘子走过去把介绍信递给她看。
离得近一些后,我看这女子的脸被烧祭的火光衬托得红扑扑的,这倒让我少了一丝顾忌。她接过信后就当着我俩面,打开仔细瞧瞧。我和潘子没说啥,静静等着她看完。我发现这女子看介绍信时,表情有点古怪,貌似有一种犹豫的神色在眉间出现,也不知道她脑子里琢磨啥呢。我也猜过,难不成刚才那鬼笑就是这妞儿叫唤出来的?但我立刻把这想法否定了,刚才出现鬼笑声的地方,离这很远,就算她嗓门再大,练成了传说中的狮吼功,也可不能把笑声传出去。
女子看完信后,把它折起来递给我说:“我也是绥远村的一名老师,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这样吧,你们等我把纸钱烧完,我带你们去绥远村。”我一听这话,心说那感情好啊。本来我和潘子打定主意在旁边站着看她烧纸,但她却突然提出一个要求,让我俩跟她一起烧。这要求挺难为人的,我跟坟主都不认识,烧个什么劲啊?不过看那女子一脸严肃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我和潘子互相瞧了瞧,只好再依了她一次。
为了能烧得快一点,我一把一把地抓纸钱,往火堆里丢,这期间女子一度停下来几次,扭头注视着我俩,这让我觉得,她让我俩烧纸钱是小,借机近距离观察我俩才是真的。等纸钱烧完了,拜祭结束了,她又把木盆抱起来,招呼我俩跟她走。我一看她走的方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她带我们往里走,说白了,这么走下去,岂不是离那土路越来越远了?潘子也察觉到不对劲,他吆喝一声把女子喝住,指了指身后。
这女子挺聪明,知道我俩啥意思,解释说,走土路其实绕远了,这里有近路,跟她走不出半小时就能赶到村里。我半信半疑的,还想接着问几句。不过她说完就闷头往前走,大有不再搭理我俩的意思,我和潘子无奈,只好跟着。我俩都保持警惕呢,一旦遇到啥不对劲的,我敢保证会第一时间扭头就跑。
这女子走路怪怪的,迈步特别小,走的是那种只有古代才流行的小碎步,这么一弄可好,我和潘子只能慢悠悠地在后面跟着,尤其我发现我俩还不能盯着她脚步看,不然有种要学她走路的冲动。估摸过了二十多分钟吧,我们来到一个下坡,我望了望发现眼前真是一个村子。而且村里一看就没通电,整个黑压压一片,跟刚才那片坟包一样,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女子估计是走累了,站着歇了一会,趁空跟我俩说,一会先带我们去吃点东西,再找个住的地方,等休息一晚,明早再带我俩去学校报道,但进村时要注意,一定别喧哗,不然村里的狗醒了,就会乱叫,那样太扰民。
我和潘子都点头应着,我发现潘子有点心不在焉的,等我们继续启程时,我问,他刚才想啥呢。潘子跟我没啥可避讳的,把头凑过来低声说:“杜睿,我咋觉得不对劲呢,你说绥远村和那片坟场分布的那么像,不会说这村子就是那片坟场吧?”我被潘子这话刺激到了,脑神经都跟着砰砰乱跳。我想起赶驴车老头的话了,绥远村闹鬼,但就算它真是个鬼村,为了任务,我们也不能退缩。我口不对心地回了潘子一句:“你想多了!”
没多久,我们仨就下了坡,来到村子里。之前隔远看,这村子只是黑漆漆的,但真等身在其中时,我更觉得不对劲了。这里异常地肃静,甚至毫不夸大地说,就是一片死寂。我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直觉在作怪,总觉得有个人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窥着我们。我四下看了好几次,想验证自己的猜测,却一直没有什么发现。潘子也有点一惊一乍的,眼睛左顾右看,特别紧张。
白衣女子先带我们来到一个瓦房前。这瓦房很破,窗户没玻璃,都是用塑料布蒙的,有些地方都裂了好大一个口子。等我们进去后,借着微弱的烛光,我看到这里摆着一个大圆木桌子和几个老式长板凳,在犄角还有一个炉灶。我心说这就该是绥远村的一个小饭堂。
那女子让我俩先坐下,她给我们弄吃的。这种长条板凳坐起来很不舒服,稍微一动身子,都吱吱乱响,弄得我都不敢坐实了,怕它禁不住塌了。潘子不想说话,就把手放在圆木桌子上:“哒哒哒”、“哒哒哒”地有节奏地敲着,我也没理他,趁空跟女子聊了几句。毕竟走了这一路,我跟她算认识了,总不能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吧。
她告诉我,她叫刘卉,让我俩叫她小卉就行,而且说话的功夫,她从锅里舀出两碗汤,给我俩端过来。我接过碗,发现还是温的,不过当我盯着里面时,心里犯迷糊了。因为汤看着怪怪的,黄黄的,还掺杂了一些黑粒,跟浆糊一样稠。我回忆一下,还真想不出这是什么做的,我又看潘子,他真饿了,早就端起来喝了一口。
看我一直看着潘子也不喝汤,刘卉念叨一嘴,说这汤是用土豆熬出来的,绥远村周边环境恶劣,只有像土豆这类农作物才好种,让我别挑食,多担待一些。我倒没像她说的那么娇性,最后也学着潘子那样,把汤喝了。接下来她又带我们去了村子靠边的地方,在另一个瓦房前停下来。她指着这瓦房说,这是我俩以后住的地方。
刘卉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教工宿舍了,可我望着这房子,眼睛都快直了。它很小很窄不说,上面瓦片都有碎的。如果赶上阴天下雨,我怀疑外面下大雨,房里面也得下场小雨,或者一场大风刮过来,它都得被吹塌一块。刘卉没有领我们进去的意思,她又嘱咐我们两件事,一是让我俩夜里千万不要在村里乱走。另一个她特意指着后山告诉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去转悠。这俩规矩让我摸不到头脑,尤其不能去后山这个规定,一下让我想起那断层石碑了,石碑上说禁地危险,难道这禁地指的就是后山么?
刘卉没多待,让我俩早点休息,等明天一早她再来接我俩去学校,之后又用小碎步的走法,自行离开。我目送她远去,等就剩我和潘子时,我当先去把瓦房的门打开。在刚开门一刹那,我闻到很浓的霉味,估计这里好久没住人了。我和潘子不可能就这么进去,我俩都站在门口,想先开一会儿门,放放味再说。这时潘子盯着屋里,嘴里又轻声念叨起来。
我问他念叨啥呢,他说:“杜睿,你发现没有,村里种的都是槐树,这种树阴气很重。另外你看看这屋子,窗户正对着门,甚至连床都正对门口摆放,这在风水里,可算是凶宅,很容易把鬼招来。”我不懂那些风水的知识,听潘子这么一说,也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是这么想的,管这房子吉利不吉利呢,再怎么不好也是个能住的地方,不然我俩睡大街么?
等这股霉味放得差不多,我带着潘子走进去。说来也巧,屋里正好有两个木板床,我和潘子一人一张。我选了靠里那张,放下旅行包,又拿出一条毛巾,准备好好把床擦拭一遍。这床上什么都没有,我倒不在意今晚和衣而卧,心说等明儿去村里问问,看谁家有多余的被褥,买两套就是了。
在擦床板的时候,我发现床板边缘有一片划痕,不深也不浅,我比量一下,貌似是指甲盖抓出来的。这让我挺纳闷,心说这床以前睡过什么人?怎么有挠床板的习惯呢?而且我也用指甲盖试试,发现床板本身挺硬,要不是特别用力,真都挠不出来。等把床擦完,我又把手机拿出来瞧瞧,村里一点信号都没有,也没通电,为了能留点电量,只好关机了。
随后我又拿出一支录音笔,这种录音笔是警局给我们线人特制的,内设密码,换句话说,我可以用它来录音,但想听录音内容,只有插在警局特殊设备上才能听到,而且一开启录音笔时,上面就会自动记录当天时间。在执行任务时,每天我都要对着录音笔做汇报,把调查的进度,还有这一天的遭遇说一遍。今天我录音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遇到的意外太多了,而且我也拿捏一个尺度,含蓄提一嘴,说我俩在来绥远村的路上差点没命,这么一说,是为了让李警官知道我俩有多拼命,在日后记功时,能多加点。
在录音期间,潘子走到门口,蹲在门前,好像还拿了两张纸,往门上贴。我心说这爷们又玩什么幺蛾子?录完音,我凑过去瞧了瞧,这两张纸其实就是两个门神画,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它俩挡挡小鬼。我想跟潘子说让他别费这个劲了,但又一想,他都不远万里的把门神带来了,不贴也有点可惜了,我就没管他。最后一直忙活到午夜,我和潘子才终于得空躺下来。我身子特别地乏,以为自己一闭眼睛,保准雷打不动的一觉睡到天亮。可实际上我根本睡不沉,迷迷糊糊间,我觉得身子里异常地燥热,甚至还止不住的呼呼往外出汗,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我郁闷的是,我耳边还响起了歌声,就是那神秘光碟里出现过的老式歌曲。
我想睁眼却特费劲,身子也跟麻了一样,我就一直暗中挣扎着,最后也不知道哪一下弄顺当了,蹬一下腿,才让自己解脱出来。我猛地坐起身子,大喘气,这时候脑门就甭提了,像被汗水洗过一遍,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那歌声不是梦境,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从门外隐隐飘进来的。
我看了看表,午夜两点,这大半夜的,能有人唱歌本就邪门,尤其这歌声还被那神秘光碟预言中了。我又看潘子,以为他一定也被歌声弄醒了呢,但没想到他躺在床上,睡得跟死猪一样。潘子跟我一样,也是个减刑的线人,也是从各种任务中活着回来的佼佼者,他虽然有点胆小,但警惕心不会这么弱的。我轻声喊了几句潘子,他没反应,我先压着对歌声的好奇心,悄悄下了地,来到潘子床前。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他也是一脑门汗,尤其嘴唇都干了,我就使劲推他。潘子这下醒了,而且一睁眼就带着一脸惊恐的表情,还猛地坐起身子。要不是我机灵,躲避得快,他这一下子,保准能磕到我脑袋。潘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双手四下乱摸,就好像他在确定自己还活着一样。我让他缓了一会,问他咋了?潘子说我刚才喊他时,他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娘的怎么也动不了。这情况倒是跟我刚才的遭遇一样。潘子给这怪现象下了一个结论,说我俩是被鬼压床了。
可我打心里却不这么认为,我想到昨晚遇到的那群怪乌鸦了,心说难道它们爪子上真有啥脏东西?我们被感染了?我们这次来,也带了一些药,虽然不能肯定对不对症,但我还是挑了几种,跟潘子一起吃了下去。接下来我俩又把注意力放在歌声上,这期间歌声一直没停过,那唱歌的女子也真不嫌累。我和潘子商量一下,虽然刘卉特意告诉我们,夜里不要乱走,但我和潘子没管那么多,打算坏了这个规矩,出去一探究竟。
我俩稍作整理,把弹簧刀都提前攥在手里,一同往门前走。我本来听着歌声心里暗暗得意,心说她有本事就这么唱下去,只要再给我俩半分钟时间,就能把她逮出来。可在我刚摸到门把手一刹那,歌声停了,尤其原来还正唱在高调上呢,明显是突然中途停止的。我有些傻眼,跟潘子原地不动等了一小会,我还期盼那歌声会再次出现,但让人失望的是,屋外一直没什么动静了。
我和潘子又商量,我的意思就算找不到声源了,我俩也该去外面走一圈。潘子同意了。开门时,我俩还都故意踮着脚。屋外的景象没啥大变化,依旧是死一般的沉默。我们就站在门口四下打量,除了对面有一个瓦房外,其他瓦房离我们这里有点远,我一分析,歌声从那里传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对潘子打手势,我俩奔着对面弓着腰跑过去。
虽然都是瓦房,但这瓦房可比我们住的那个好多了,连窗户上的玻璃都被擦得崭亮,月光照在上面隐隐有些反光。这么好的房子,我猜主人在村里地位一定不低,我合计来合计去,想拿口渴为借口,敲她家屋门试探试探。我刚开始没太用力,只是有节奏地敲几下,但屋里压根没反应,我心里奇怪,又加重力道,甚至最后还用拳头在上面砸一下。
潘子一直在我旁边等着,他看还没反应,急了,指着窗户说:“你等下,我去看看。”虽然趴窗户不太礼貌,但现在也没啥别的法子。潘子悄悄来到窗前,他这一趴可真不客气,整个脸都快贴在玻璃上了,但屋里实在太黑,他根本瞧不清什么状况。他又摸出事先带着的电筒,对里面照了照。我没在窗前,也不知道具体啥情况,等潘子观察一番后,跟我形容说:“根本没人住,但明显被人打扫过,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被潘子弄出好奇心了,又试着拽了拽门把手,发现上了锁。
我在监狱服刑时,跟其他狱友学了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尤其是撬锁的本事。我后腰特意带着一个小工具夹,里面都是铁丝和硬卡片这类的玩意儿。我先四下看看,再次确定周围没人偷窥后,蹲下身瞧着门锁,这就是一般的A级锁,撬开并不难。我把卡片拿出来,对着门缝塞进去,等上下一滑确定门锁准确位置后,又对着锁舌用力一顶,把它弄开了。
我和潘子蹭了蹭鞋底,潘子打着电筒带头,我俩一前一后钻进去。不得不说,这屋子里不仅很干净,还飘着一股香气,我俩也不用商量,很默契地分头翻找起来。我发现在角落里放着一台老式唱片机,这在现在来说,都有点古董的意思了,尤其它那大喇嘛型的脑袋,怎么看怎么别扭。我突然有一个疑问,心说村里不是没电么?这唱片机买来有什么用?还是说村里通过电?
我一时间想不明白,这时潘子有了发现,招呼我过去看。他正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放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站着三个女人,一个是女孩子,梳着小辫,另两个都是中年妇女,有个妇女还出奇地胖,腰都跟水桶有一拼了。我本来挺纳闷潘子为啥叫我,心说这照片弄不好都比我俩岁数大,我能认识这上面谁是谁啊,但等仔细看看,发现那个小女孩双眼间有一颗黑痣,她竟是小时候的刘卉。
较真的说,这也不算啥特大发现,无非说明刘卉跟这房子的主人认识,甚至有密切的关系。可要联系起来看的话,我总觉得,刘卉肯定知道那鬼笑的事,也清楚那歌声是怎么来的。我和潘子又翻找一会,就再无其他发现了,我一合计,这次任务就从刘卉身上下手吧,明天见到她时,多套套话,一定能有进展。我们又小心地退出去,我俩都是手脚干净的人,这房子进来时什么样,出去时就什么样。等回到住的地方,我一时间没其它念头了,就寻思快点睡,养足精神再说。
可我俩刚躺下没多久,潘子又坐了起来,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被他吓了一跳,尤其他那眼神,都瘆得慌,我就问他干啥。潘子有点愣,在我问完好一会,他才猛地缓过神来,跟我说:“我咋想尿尿呢?”我算服了这爷们了,刚才他出了那么多汗,晚上也没咋喝水,怎么夜里还来尿意了呢?我看这屋里也没尿盆,就跟他说:“你去外面找个空地,随便解决一下不就得了?”潘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让我陪他去一趟,这村里古里古怪的,他怕自己出去有危险。这理由让我无法拒绝,而且我也真不想潘子出事。
我俩出去后,绕到了瓦房后面,这里就是一片荒草地。我趁空还跟潘子念叨一句,让他晚上看人别直勾勾的,太吓人了,可潘子听完我这话显得莫名其妙,反问我,谁看人直勾勾的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打马虎眼,也就权当随便提一嘴,并没太深究。就当潘子刚解完手时,有一阵微弱的笑声从远处传过来,是呵呵的那种,跟之前嘻嘻嘻的鬼笑声又不太一样,要不是我俩敏感,这笑声极容易被忽略掉。
潘子正拉“鸡架门”呢,被这笑声一吓,都乱分寸了,一下拉快了,我也没看清他把哪碰到了,反正难受的哼了一声。随后他来了火气,不过更有点害怕,用一副稍微变声的语调跟我说:“这鬼笑太他妈变态了,一路跟着咱们不说,到村里咋还变味了呢?”我倒没像潘子这么想,我品着刚才笑声的来源,觉得它好像是从我们对面瓦房那边传过来的。
我就说:“反正你也尿完了,咱们再去对面看看。”潘子脸色有些不对劲,问我:“咱们不是刚从那里回来么?屋里也没人啊。”我回答不上来,满脑子也是这种疑问。我俩踮着脚又往那边走,不过还没等我们到地方,就听到那瓦房后面传来轻微的说话声。这说明瓦房后面有人,我俩互相示意轻点声,又贴着墙壁往后面绕,等趴在墙头一看,这里有口井,有个胖老太太不知道啥时候来的,正背对着我俩,臃肿地坐在井旁边。
只一眼,我就看出来,这胖老太太是照片里的那个胖中年妇女,没想到岁月如梭,她现在已经是个老人了。她根本没留意我俩在偷瞧她,手里攥着一页纸,一边看一边扭头冲着井自言自语。我和潘子没动弹,全静静听她说些什么。她对井边说了这么一句话:“张家大婶,你儿子让我问你,还缺钱不?用不用他给你再烧点。”随后她又故意把脑袋往井边探了探,嗯嗯哈哈应了几声后,又看着纸往下问另外一个问题。
她这举动可把我和潘子吓住了,这不明显跟死人对话呢么?尤其那井里,难道真躲着一个鬼不成?潘子更是忍不住把嘴捂住,差点呜出一声来。或者是潘子这么一捂嘴,弄出什么小响动来了,那胖老太太突然停下来,狐疑地扭头往我们这边看。我俩不可能被她发现,都急忙缩回脖子。这时候我有点小紧张,特意竖着耳朵听着,怕那老太太往我们这边走。不过我担心的情况没发生,不一会儿,她又开始念叨上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甚至都快产生幻觉了,总觉得有个冰冷的手在摸我后脊梁骨似的,我对潘子使眼色,我俩陆续后退,悄悄回到自己屋子里。潘子回去后就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虽然没说什么,但能感觉出来,他压力很大。我也觉得这次任务太棘手了,刚来绥远村的第一晚,我们就遭遇这么多古里古怪的事,尤其更是遇到一堆破解不了的谜团。我有种直觉,黑白照片里的三个人,刘卉和胖老太太都已经出现了,另外那个妇女,我们早晚会见到她,甚至她也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跟我们见面的。
我躺在床上,想着想着,最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刘卉就过来敲门了。只隔一晚上,她变化蛮大的,昨夜穿着一身白衣白裤,看着阴森森的,跟女鬼有一拼,今早却换上一身花格子的连衣裙,还梳了一个刘海,显得阳光多了,尤其那刘海还把黑痣隐隐挡住了,另有一番韵味。
她跟我俩闲聊几句后,突然一转话题,问我们昨晚有没有不守规矩去村里转悠。这我能承认么?就算她真发现什么,打心里知道我俩出去了,面上我也装迷糊。潘子跟我一样,装傻充愣地摇头否认。她也没再多问,等收拾妥当了,又带着我俩出了门,说一起去吃早饭。在刚走出去时,潘子回头看了一眼,咦了一声。我顺带着回头看一眼。屋门上那两个门神没了。
这门神可是潘子很认真地贴上去的,就算刮大风,也不会这么轻易把它们吹跑。我纳闷,难道后半夜真有人来过,还顺带把门神撕走了?
我们吃早饭的地方还是那个破瓦房,昨晚喝土豆汤的地方,这次随着刘卉进去时,我发现那圆桌子上坐了两个人,正捧着一碗粥喝着,另外炉灶前还站个老太太,看样正在煮饭。我一看她那胖劲儿,心里咯噔一下,就是昨夜在井边疯言疯语那老太太。好在她根本不认识我俩,我和潘子也没跟她说啥,不然我俩带着惧意,说话声一变,容易露馅。
刘卉给我们介绍,说喝粥那两个也是老师,是我俩同事。我们仨找个地方坐下来,刘卉还捧来三碗大米粥,在喝粥期间,她说起正事,绥远村的学校规模很小,一共才三十来个学生,根本没有体育课,不可能让我俩做体育老师。我就顺着问了句,不做体育老师,我俩还能教啥?她说目前各缺一名数学、语文老师,估摸也看出来了,我俩没啥文化底子,她还特意叮嘱,在绥远村教书,都是小学课本,不难。
我心里合计,如果只教小学课本,我俩还真能凑数,小学数学那玩意儿,无非是加减乘除嘛,甚至都不用方程式,相比之下,教语文可比数学难多了。语文这东西,最爱咬文嚼字。我仗义一把,让潘子先选,问他教啥,其实打心里我都很肯定了,潘子一定会选数学。可潘子表情很沉,闷头想了半天才跟我说:“杜睿,你教数学,我弄语文。”我一听这话,心说得了,潘子啥智商啊,连小学数学都玩不明白。
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吃完刘卉带我们去学校转了转。要我说村里学校何止规模小啊,它压根就没规模。两间大瓦房,被一大片篱笆墙围着,大的那间当教室,小的那间当教师办公室,这就算学校了。一群个头参差不齐,年龄有大有小的学生,都挤在同一个教室里上一样的课。
刘卉说今天上午是数学课,我得跟着去听课,而潘子呢,只好在办公室呆着,跟其他老师交流交流。这是要把我俩分开的节奏,虽然我不想这样,但找不到好理由了,只好拿着笔和本,跟刘卉一起走了。
我从没当过实习老师,对该做啥、不该做啥,一点都不懂,但我上学那会,见过别的老师听课,他们都坐在最后排。我就照葫芦画瓢,也凑到后面。刘卉今天讲的是应用题,我这是第一次实习,不管真假,也得做做样子不是?我就对自己说专心点,弄弄笔记啥的,但我真高估自己了。没到二十分钟,我俩眼皮就开始往下耷拉,总觉得刘卉讲课跟唱催眠曲一样,把我无限的困意都引了出来。我暗自鼓劲,自己一定撑住,别掉链子,但十分钟后,我霸占旁边学生桌子,趴着睡着了。
我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睡多久,反正突然觉得不对劲,这教室怎么变得静悄悄的,讲课声哪去了?我心说难不成刘卉讲完课,改成上自习了?我就抬起头,眯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四下瞧瞧。
这一看把我吓得够呛,整个教室的学生全站起来,直勾勾看着前方,刘卉在讲台上同样直勾勾的望着台下,他们一起双手掐腰,很夸张的乱扭着脑袋。就说挨着我的这个学生,他晃脑袋那幅度让我都担心能把脖子掰断了,尤其他还微微裂开嘴,露出一副稍有狞笑的表情。这下让我想起狰狞女尸了,心里扑通扑通乱跳,也没睡意了,更不敢盲目碰这个学生,怕出啥状况,我慢慢站起来,对着刘卉摆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