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阁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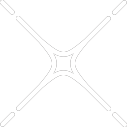
萨拉永远都忘不了在阁楼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她承受着剧烈的、孩子无法承受的哀痛。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种痛苦,没有人会理解。幸好,在她清醒地在黑暗中躺着的时候,周围陌生的环境偶尔能分散她的注意力。如果不是她那小小的身体使她想起还有物质的东西,她那幼小心灵里的痛苦会更大,那可不是一个孩子所能承受的。事实上,这一整夜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除了一件事之外的任何事情。
“我没有爸爸了,”她不断地喃喃自语着,“我没有爸爸了!”
过了很久,她才感觉到床竟是这么硬,她不得不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寻找一块能够安稳睡觉的地方。她感到屋里的夜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黑,冷风在屋顶的烟囱之间呜咽,就像是有人在大声哭泣。还有比这更糟的,那就是墙壁内和踢脚板后面有东西在打闹,发出搔抓的声音和吱吱的叫声。萨拉知道这是什么,因为贝基以前描述过这些情况——大小老鼠在一块儿打架或者玩耍。甚至有一两次,她听到了有着尖锐脚趾的脚在地板上乱窜的声音。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回忆往事的时候,想起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吓得浑身发抖地从床上坐起来,再次躺下的时候用被子捂住了头。
她生活的巨变不是慢慢发生的,而是突然降临的。
“她得马上开始干活,因为她得挣钱吃饭。”明钦女士和阿米莉亚小姐说,“马上告诉她,她要做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马里耶特就离开了。萨拉经过自己原来房间的时候,房门打开着,她朝里头看了一眼,里面的一切都变了。她的各种装饰品和奢侈的衣物都已搬走,房间角落里放了一张床,这间房成了一个新学生的卧室。
她到楼下吃饭,看到拉维尼娅坐在明钦女士身边那个原属于自己的座位上。
明钦女士冷冰冰地对她说:“你得开始你的新工作了,萨拉。你在小桌子那儿和较小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你务必要让她们保持安静,并且让她们遵守秩序,不要浪费食物。你应该早些下楼,洛蒂已经把她的茶打翻了。”
这只是个开始,随后,交给她的任务一天比一天多。每天她至少要做的是教幼小的孩子们法语,辅导她们其他的功课。明钦女士发现很多地方都能用到她。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天气,都可以吩咐她去办事,可以让她去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厨子和用人们学着明钦女士的口气,把这个以前被人们吹捧的“小姑娘”支使来、支使去。她们是下等的仆人,脾气很坏而且没有礼貌,如果犯了错,可以很方便地把责任推给身边的什么人。
在最开始的一两个月里,萨拉认为,只要她努力把事情做好,受到斥责也不反驳,或许会让那些使劲儿使唤她的人温和一些。在她那幼小但高傲的心灵里,她想让他们明白,她要努力地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赏赐。但后来她终于明白了,没有一个人能被软化;她越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别人安排的事情,那些粗鲁的女佣就越是盛气凌人、越是苛刻,而那个爱骂人的厨子更是动不动就责骂她。
她要是年龄再大一些,明钦女士肯定早就让她教年纪大点的姑娘们了,这样就能解雇一位女教师来节省开支;不过她看上去仍然像个小孩子,所以让她当个干杂务的上等小丫头和干各种工作的女佣会更好。一个普通的小男佣可没有她那么聪明可靠。人们可以把困难的任务和复杂口信的传递放心地托付给她。她甚至还可以出去结账,可以打扫房间、整理东西。
她的学生生涯已经过去了,现在可没有人会教她什么。她每天都被别人指挥得跑来跑去,干这干那,只有在这样忙碌一整天之后,才勉强允许她晚上带着一摞旧书去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面自学。
“要是我不经常温习一下以前学过的知识,恐怕就会把它们全忘了。”她跟自己说,“我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厨房小帮佣了,如果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厨房帮佣,那我跟可怜的贝基还有什么不同?我怕我会把所有的知识都忘了,会在说话的时候开始不发‘h’这个音,会忘记亨利八世有六位妻子。”
在萨拉的新生活里,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她在学生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了。她再也不是她们之中高人一等的人物了,好像已经不再是她们的一分子了。人们随意地支使她,没完没了地让她工作,她几乎没有机会与学生们中的任何人说话,而且她不可能不明白——明钦女士希望让她过那种远离教室占有者们的生活。
“我绝不让她和别的孩子关系亲密,也不许她与她们说话。”明钦女士说,“女孩子们都爱抱怨,要是让她讲述自己的荒唐故事,她肯定会把自己描述成故事里受尽虐待的女主角,这会给孩子的家长们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独自待着——过一种适合她现在处境的生活。我让她留了下来,给了她家,这远远超过了她能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
萨拉并没有期望太多,她的自尊心很强,她不想继续跟那些对她有明显敌意和游移不定的女孩子保持亲密关系。实际上,明钦女士的这些学生都是些愚钝而平凡的孩子。她们过惯了富足舒适的生活,但是萨拉穿的衣服却显得越来越短小,越来越破旧,变得非常古怪。这一切已经变成了事实,她脚上穿着破了洞的鞋子,胳膊上挎着篮子,被厨子吩咐去街上买一些急需的东西,所以那些学生在跟萨拉说话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像是在和下等仆人说话。
“看呀,她就是以前那个有钻石矿的小姑娘。”拉维尼娅说,“她的确是太可笑了,而且看起来比以前还要奇怪。我一直都不喜欢她,但是我受不了现在她那种看着人不说话的模样——就像是想从你身上发现点儿什么。”
“我的确是这样的,”萨拉听到这话的时候马上说,“这就是我总盯着一些人看的原因。我想了解她们,之后就仔细地、反复研究她们。”
其实,有几次她就是因为多观察了拉维尼娅一会儿,才使自己避免了麻烦。因为拉维尼娅总是想找碴儿,她觉得要是能捉弄一下以前那个“装点门面的学生”,会使她非常高兴。
萨拉自己从不捣乱,也不会干涉别人。她像苦工似的工作:她在下雨的街道上拿着包裹和篮子迈着沉重的步伐,她卖力地给那些年纪小的、上课不专心的学生们上法语课。由于她的衣服越来越破,样子也变得更加凄惨,所以人们吩咐她最好在楼下吃饭。她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孩子,她的内心越来越孤傲,也越来越痛苦,但她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军人们不会抱怨,”她紧咬着牙关说道,“我也不会抱怨。我会假设这是战争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时候,幸亏有三个人能安慰她,否则孤独几乎就要把她幼小的心给撕碎了。
第一位肯定是贝基——恰好就是贝基。在那个阁楼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她一直模糊地感到安慰,知道那面有老鼠乱窜、乱叫的墙壁那边还有一个小家伙。之后的几天夜里,她觉得这种安慰感越来越强。白天,她俩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各人有各人要干完的活,要是被发现,还会被认为是偷懒和浪费时间。
“小姐,您不要怪我,”第一天清晨,贝基悄悄地跟萨拉说,“我没说什么客气话。要是我说了,就有人斥责我们了。我是指‘请’、‘感谢您’和‘对不起’之类的话,不过我也不想花时间说这些。”
不过,在天亮之前,她经常偷偷跑进萨拉的阁楼里,帮她系衣服扣子,或者先帮萨拉做些需要帮助的事情才会去楼下的厨房里生火。每到晚上,萨拉总能听到谦恭的敲门声在她的房门上响起,这说明如果她需要,贝基就又会来帮她。前几个礼拜,萨拉觉得自己已经悲伤到神经麻木,甚至不能谈话,因此一段时间之后她们才开始经常见面,或是互相看望。贝基明白,不要去打扰悲痛中的人们,最好让他们独自待着。
艾芒加德就是三名安慰者中的第二位,不过在艾芒加德明白自己应该怎样与萨拉相处之前,发生了一些古怪的事。
当萨拉从痛苦中逃离出来,重新开始注意周围生活的时候,她都已经忘记了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艾芒加德。过去她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不过萨拉觉得自己好像比她大好几岁。毋庸置疑的是,艾芒加德既重感情又迟钝。她单纯又情不自禁地依恋着萨拉;她会带着功课去找萨拉帮忙;她认真地听着萨拉的每一句话,缠着萨拉给她讲故事。可她自己却没有什么有趣的话可以说,她讨厌所有的书籍。当人们遭遇重大变故的时候,根本不会记起有这样一个人,因此萨拉把她忘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芒加德突然被叫回家里住了几个礼拜。她回来之后,一连两天都没见到萨拉。她第一次碰到萨拉的时候,萨拉恰好从走廊上过来,双手抱着一大堆衣服要送到楼下去缝补。萨拉已经学会了自己缝衣服。她的脸色苍白得像变了一个人,并且仍然穿着那件古怪的又短又小的黑色连衣裙,露出了长长的黑腿。
艾芒加德是个反应很慢的姑娘,根本应付不了这样的情况。她实在想不出要说些什么。虽然她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她也绝对想象不到萨拉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么古怪、这么可怜,简直像个用人。她觉得伤心极了,却又无可奈何,只是突然激动地大声笑了一下,并大声喊道——这喊声毫无意义,似乎也没什么目的。
“哦,萨拉!是你吗?”
“是的。”萨拉答道。突然,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这念头使她满脸通红。
萨拉双手抱着那堆衣服,将下巴抵在上面,以免衣服掉下来。她那目不转睛的视线里有一种东西,这让艾芒加德更加手足无措,觉得萨拉好像变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人。或许是因为萨拉一下子变得很穷,必须去缝补衣物,像贝基一样干活了吧。
“哦,”艾芒加德磕磕巴巴地说,“你怎么——你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萨拉答道,“你怎么样?”
“我——我很好,”艾芒加德害羞得不知所措,随后,她突然想到得说些听起来比较亲切的话。“你是——是不是过得不好?”她不假思索地问。
听到这句话,萨拉觉得自己遇到的一切都很不公平。这时候,她那饱受折磨的心灵被怒火填满了,她认为要是有人笨成这个样子,那还是离她远一些的好。
“你认为我怎么样?”她反问道,“你以为我过得很好吗?”之后她没再说话,从艾芒加德身旁大步地走过去了。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萨拉逐渐意识到,要不是这苦痛的经历让她忘记了一些事情,她真不应该因为艾芒加德那种笨拙的说话方式而责怪可怜又迟钝的她。艾芒加德一直是那么笨拙,而且她越是觉得自己笨,就越是愚蠢得出奇。
但是那时萨拉脑海里突然闪现的念头使她变得过分敏感了。
“她跟其他女孩一样,”萨拉心想,“她知道其他人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所以她也并非是真的想和我说话。”
所以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她们之间出现了隔阂。她们偶然碰到的时候,萨拉会看向别的地方,而艾芒加德则会十分局促,窘迫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有时候她们彼此点一下头就走过去,有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她要是不想跟我说话,”萨拉想,“那我就不见她。明钦女士的做法使这点很容易办到。”
明钦女士的办法的确很有效,后来她们几乎很难见面了。这时候,人们发现艾芒加德比以前更迟钝了,看起来无精打采、愁眉苦脸。她常常坐在窗边的座位上,抱成一团,静静地看着窗外。有一次,杰西从她身边走过,好奇地停在那儿看着她。
“你怎么哭了,艾芒加德?”她问道。
“我没哭。”艾芒加德用一种低低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道。
“你就是哭了,”杰西说,“一大颗眼泪从你鼻梁上滑下来,然后从鼻尖上掉下来了。瞧,又是一颗。”
“噢,”艾芒加德说,“我难受极了——谁都别来打扰我。”她把胖胖的后背转过来,直接拿出手帕盖在脸上。
这天晚上,萨拉回到阁楼的时间要比平时晚一些。人们一直使唤她干这干那,直到学生们都回房间睡觉之后,她才去一个人都没有的教室里学习。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阁楼门下透出一点微光。
“除我以外没人来这儿啊,”她马上这样想,“可是有人点着了蜡烛。”
确实有人点着了一支蜡烛,而且不是她在厨房烛台上用的那种,是学生卧室里用的那一种。有个人穿着睡衣,披着披肩坐在那只破旧的凳子上。这是艾芒加德。
“艾芒加德!”萨拉大声喊道,艾芒加德被这突然的一声给吓坏了。“你这样会有麻烦的。”
艾芒加德从脚凳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她穿着一双大得离谱的拖鞋走过来,哭得眼睛和鼻子都是通红的。
“是的,我明白要是被发现就会有麻烦。”她说,“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根本不在乎。噢,萨拉,请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了?”
她声音里的某些东西使萨拉的喉咙被以前出现过的东西哽住了。她说的话那么亲切、那么朴实,跟以前那个要做萨拉“最好的朋友”的艾芒加德是那么像。这话听起来并没有前几个星期里,萨拉感觉到她要表示的那种意思。
“我真的喜欢你,”萨拉答道,“本来我以为——你知道,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了。我以为你——也变了。”
艾芒加德睁圆了那双流泪的眼睛。
“不是,是你变了!”她大声说道,“你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家回来之后你就变了。”
萨拉思考了一会儿。她终于明白是自己错了。
“我是不同了,”她解释道,“但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不同。明钦女士不许我和别的女孩接触,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想和我说话。我以为——或许——你也不想,因此我才故意避开你。”
“噢,萨拉!”艾芒加德像被责备了似的,沮丧得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之后她们对望了一眼,跑上前拥抱在了一起。必须说明的是,萨拉那满是黑发的小脑袋在那披着红色披肩的肩膀上待了好几分钟。当初她以为艾芒加德抛弃她的时候,是那么孤独!
随后,她们一起坐在地板上,萨拉双手抱着膝盖,艾芒加德裹紧了披肩,崇拜地看着萨拉那张奇怪的、长着大眼睛的小脸。
“我受不了,”艾芒加德说,“我敢肯定没有我你也能活下去,萨拉,可要是没有你,我可不行。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被子里哭的时候,突然就想到溜到你这儿来,恳求你允许我们再做朋友。”
“你比我好多了,”萨拉说,“我自尊心太强了,不会尽力去交朋友。你看,现在考验来了,这些考验证明了我并不是一个好孩子。我一开始就担心它们要这样证明,也许——”她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也许这些考验的到来就是为了证明这个。”
“我看不出来它们哪点儿好。”艾芒加德坚定地说。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萨拉坦率地承认,“可是我想,有的事情可能有好的一面,即使我们现在看不出,或许——”她犹豫地说,“明钦女士也有好的一面。”
艾芒加德四处打量了一下阁楼,她有点儿害怕,并且觉得很奇怪。
“萨拉,”她问,“你觉得自己能忍受住在这里吗?”
萨拉也看了看四周。
“要是我假设它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我就可以忍受。”她答道,“或者,我可以把这里假设成故事里的一个地方。”
她慢慢地说起来——她的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了。自从她遭遇不幸以来,想象力根本就没有发挥过作用。她觉得它似乎已经不能工作了。
“还有一些人生活在条件更恶劣的地方。想想基督山伯爵曾被囚禁在伊夫城堡地牢里,还有那些被关押在巴士底监狱里的人们!”
“巴士底监狱!”艾芒加德凝视着萨拉喃喃地说道,她听得入迷了。她记起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这些故事能给她留下印象,全是因为萨拉那绘声绘色的描述。只有萨拉能做到这一点。
萨拉的双眼中闪烁着艾芒加德熟悉的光芒。
“是呀,”萨拉抱紧了双膝说,“这是进行假设游戏的好地方。我是被囚禁在巴士底监狱的一名犯人,在这里待了许多年——好多年,所有人都把我忘了。明钦女士是监狱的看守,而贝基——”她的眼睛里忽然闪烁出了另一种光芒,“贝基也是囚犯,她住在隔壁牢房里。”
她扭过身来,面向艾芒加德,又成了最初的那个萨拉。
“我会这样假设,”她说,“这样会给我很大的安慰。”
艾芒加德感到很兴奋,也很崇敬萨拉。
“你愿意把这些都给我讲讲吗?”艾芒加德问,“晚上没人注意的时候,我可以悄悄地溜到你这里来,听你讲你白天编的故事吗?那样我们就比以前‘最要好的朋友’还要好了。”
“可以,”萨拉点点头,回答道,“灾难考验人们,我的不幸考验了你,它证明了你的为人有多好。”


